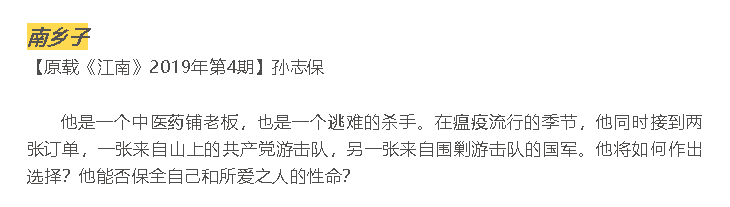我省作家孙志保创作的中篇小说《南乡子》原发《江南》2019年第4期,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9年第8期选载。
作品欣赏
南乡子(节选)
孙 志 保
“我要对你申明一点,我不是刘千叶的游击队员,我与三淮的地下组织没有任何联系。”金久说。
“可是你做的事情比一百个游击队员都多,三淮的地下党加在一起也没有你的贡献大。”林镇湘说,“我是说这一次,在此之前,你肯定做了更多的事情。”
林镇湘拉了一张椅子坐在金久对面。看着一个濒死的对手愿意敞开心扉与自己说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虽然真相的每一条触须都会像一把刀一样零割着他的心脏,但是,这样的疼痛未必不能承受。多年来,林镇湘的承受力在渐渐增大增强,已经长成一棵根深的树了。
“在此之前,”金久的声音有些缥缈,似乎声音也随着他的思绪飞走了。“我是做了一些事,但是......”金久虚肿的脸上几乎无法看到表情,只有通过像一条线一样的眼睛,窥见他内心的一些角落。
“也许,一些过去的事情对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是有用的,提起它们有些痛苦,但是,它们可以活血化瘀。林镇湘,如果我没有记错,三年前,你在长州呆过,是长州的警备司令。”金久说。
“是的,我在那里做过警备司令。”林镇湘有些吃惊,对于往事的翻检让他酸楚,却也刺激了他的好奇心。
“从警备司令到156旅的旅长,这样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虽然是一份不小的荣誉,但是,我却知道这必定不是你的本意。”金久的话像一根针,针尖扎得不深,却令人震颤。
林镇湘垂下头,用双手捂住脸。他讨厌这样的姿势,但是,它可以遮住他的表情,让暗淡的眼神消失在掌心里。
三年多了,比现在的季节早一些,好像正在闹倒春寒。长州市警备司令部情报处收到打入共产党内部代号为“鹰”的特勤人员的情报,说在第二天上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共产党的铁血杀手南乡子将要刺杀大会的主要召集人,时任长州市警备司令的林镇湘。情报处立即把情报转给了林镇湘,并建议他取消大会,或者,无限期推迟。情报处的建议对于林镇湘是一种污辱,但是,他知道它是正确的。南乡子是共产党锄奸队的头号铁血杀手,在抗战前就在长州赢得了响亮的名头,抗战期间更是以刺杀了多名日伪军政要员而令敌人谈之色变。内战爆发以后,南乡子在长州实施了十余次刺杀行动,目标都是长州市重要的军政人物,或者过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南乡子的刺杀手段特点鲜明,要么一枪致命,要么一镖封喉,被南乡子盯上的目标,生还率为零。林镇湘曾经组织过多次对南乡子的抓捕,结果都是损兵折将,以致于林镇湘的手下一听说有针对南乡子的行动,都噤若寒蝉。林镇湘犹豫了半个小时,最终决定大会按原计划召开。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上月抵达长州的陆军暂编第十一师补充兵员。半个月以前就开始筹备的大会,已经动用了各方各面的力量,将有七千名长州市民参加,如果轻易取消,不仅招兵计划无法完成,林镇湘的名声也将严重受损,甚至影响政治前程。林镇湘只有硬着脖子往前走,当然,他在脖子上套了很厚的防护,即便有刀落下来,也无法在脖子上留下一道白痕。林镇湘不相信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之下,南乡子还能得到动手的机会。
大会在长州市政府楼前的大广场举行,林镇湘动用了他能动用的所有力量把会场变作了一只铁桶。七千人的大会,所有参会者都要被搜身,任何金属制品都会被当场没收,略有嫌疑便会被当场拘捕。在主席台的周围,林镇湘的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呈扇面展开,就像一百条德国牧羊犬一样环伺在主人周围。林镇湘还作了另一个准备:把原定一个小时的大会缩短为半个小时,既完成了计划,又体面地保全了自己。林镇湘想不到,集会开始不到十分钟,便有三发子弹像三只黑色的鸟儿一样哗哗叫着向他飞来,在他的胸膛上凿出了一个小小的等边三角形。林镇湘倒下了,三只鸟儿把他击倒在地,却没有洞穿他的胸膛,因为他设置了一道厚重的闸门:把一块巴掌大的像一朵莲花一样的镔铁藏在了胸口。林镇湘知道南乡子的暗杀习惯,南乡子使用枪弹的时候,唯一的目标是心脏,如果是一发子弹,就正中靶心,如果是三发,就是等边三角形。南乡子如果射出三发子弹,就意味着他对刺杀对象极端仇恨,三发子弹可以放大痛苦,制造的图案像一张彩色的张贴画,可以把刺杀效果渲染到极致。三颗子弹都穿透了厚厚的镔铁,但是,已经无力在林镇湘的心脏里走得更远。
尽管在广场的四周布满了军警,南乡子还是逃脱了,当然,他也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他的两名助手为了掩护他而当场殒命,而他自己,好像也中了一枪,在他逃跑的路线上,发现了点点滴滴的血迹。
躺在医院里的刚刚回到生死线这一侧的林镇湘用微弱的声音下达了全城搜捕令,不到一天,便有一百五十人死在他的枪下。其中有多少共产党?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这样的杀戮是必须的。就像打靶一样,你不可能每一枪都打在十环上,七环或者六环,都是可以接受的,跑靶又有什么呢?那是为打中十环而作的不可缺少的准备。血腥之举对于林镇湘来说既是报复,也是对声誉的弥补。当着七千人的面被南乡子连击三枪,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无法向上峰和民众交待,唯一的办法就是搜捕,就是枪杀。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他逆转局面,一个月以后,他刚刚可以下床,就被免除了职务。
幸亏有几个当权的老上司为他说话,免职不到一个月,他便被调到156旅当了副旅长。半个月以后,旅长在一次对三淮山的围剿行动中被一粒子弹击中了太阳穴,当场殒命。林镇湘感谢那粒子弹,因为它间接地把他送到了旅长的宝座之上。
“你好像对我的事情很了解,”林镇湘说,“你是长州人吗?或者,在长州呆过?”
“我不是长州人,我的老家是苏州。”金久努力地有些滑稽地噘了一下嘴,说,“但是,我是南乡子。”
林镇湘用力睁大了眼睛,这个动作使他避免了一声惊讶的叫喊。
林镇湘站起身来,拔出手枪,一步步逼近金久,把枪口抵到金久的前额上。金久的眼神非常淡定,林镇湘知道,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人在死神面前不可能有这样的眼神。那么,他刚被带到三淮山时的恐惧和不安是装出来的,甚至他的冷汗都是任他驱使的。林镇湘知道自己无法不相信金久的话,面前这个被毒药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中年男人,正是他一生最大耻辱的制造者,南乡子!
林镇湘长叹了一声,痛苦地摇了摇头,把手枪插回腰间,重新坐回椅子。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一切动作都是无用的,而在他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怯懦也是无所谓的,哪怕失声痛哭也不能算是丑陋,因为南乡子的眼睛永远是居高临下的。
“你是我的梦魇,”林镇湘说,“三年过去了,你又用三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刺杀你,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失手,”金久说,“而且,我还折了两个同志。我不相信你还活着,但是,当我在三淮城里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自信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林镇湘坐直了腰杆,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忽然笑了,说,“你的枪法没有问题,这里现在还有三只乌鸦在飞。”
金久缓缓地长叹了一口气,说,“由于出了叛徒,在接下来的大搜捕中,我的组织遭受了重大打击。无奈之下,我带着女儿逃出了长州,在三淮做了一个药铺老板。”
“我想知道,你的枪来自哪里?”林镇湘问。这个折磨他三年多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看到答案了。
“广场边缘躺着几株快朽的老树干,你还有印象没有?”金久问。
林镇湘恍然大悟。广场的南缘横放着几株快朽的老树干,有一米左右的,也有两米左右的,干干净净,似乎是被附近居民有意放置的,目的似乎很简单:晚上散步时,可以歇歇脚。
“但是,那些树干一直在那里,不是临时.......”话一出口,林镇湘就感到自己很愚蠢。树干从什么时候起呆在那里不重要,关键是它们为南乡子的枪支提供了隐藏地点。
金久的回答更令林镇湘感到自己的愚蠢:“在长州城里,有很多这样的树干,是我的助手有意放置的。它们不显山露水,就像是环境的一部分,当我们需要时,里面就会出现我们用得着的武器。”
“如果我的人把你击毙了,就没有今天的事了。”林镇湘恨恨地说。
“你的士兵打伤了我的左腿,让我无法再以一个杀手的身份继续工作,这是三年以来我最大的遗憾。不然,你在三淮城的第二年就可能成为淮河岸边一堆黄土下面的孤鬼。而且,如果我当时死了,你的染上瘟疫的士兵今天找谁救治呢?”金久嘲讽地说。
“是的,今天他们的病情有了好转。”林镇湘说,“但是,你别指望我能宽恕你。这些日子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要如实地向我招供。如果你是健康的,我已经把你凌迟了,根本就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金久轻蔑地看着林镇湘。
金久带着女儿从长州逃出来以后,在距离长州城六十余公里的一个叫盐关的古镇养了半个月的伤。他委托当地的老乡到长州了解情况,老乡带回的消息令他痛不欲生。长州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长州城里到处都是缉拿南乡子的布告,四个城门每天都会悬上新的尸体。金久无奈,只好带着金可欣一路向北,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三淮县城。三淮山上有很多中草药,还有一支声名显赫的游击队,还有梅媛,这个地方令他感到温暖。金久的父亲是苏州城里有名的老中医,除一手金针绝活外,还以祖传的“清瘟解毒丸”而独步杏林。金久自小就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他已经像父亲一样成为苏州名医了。父亲十年前去世的时候,给金久留下一句话:仁医,仁人,择一不负终生,择二不负苍生。留在三淮城开药铺,是一个可以三全的办法:既可以实现父亲的遗愿,又可以和三淮山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还可以与梅媛长相厮守。金久曾经尝试过与刘千叶接上关系,但是,刘千叶非常谨慎,无凭无据,根本不可能取得信任。金久请梅媛在《长州晨报》上登过启事,那是原来约定的寻找组织的最后的办法,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金久想,做一个药铺老板有什么不好呢?可以治病救人,可以在不同的道路上做同样的事情。当然,如果刘千叶他们有需求,他会毫不犹豫地纵马驰援。
金久之所以给自己起绰号叫南乡子,不是因为他来自苏州,不是因为思念家乡。他喜欢那首词,喜欢那种境界。他在卧室的窗外栽了几竿君子竹,它们摇曳出的,正是他内心的感觉。他曾经幻想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在舍前舍后全部种上君子竹,而不仅仅是窗外的几竿。西风散雨未免凄清,成了林子的君子竹,会把凄清摇成朝阳。
金久说,“过往是你的耻辱,你何必过于纠结,跟自己过不去呢?”
林镇湘沉吟半晌,从衣袋里掏出半截雪茄,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刘千叶的游击队,比我的部队更早感染上瘟疫,为什么我在山上找不到瘟疫留下的痕迹?你那6000丸药,他们如果服用了,结果会惨不忍睹;如果没服用,也不会带着突围吧?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林镇湘说出了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
金久差点笑出声来:“我早就和你说过,那些药都是良心药,没有毒。刘千叶的游击队有足够的战斗力冲破重围,与那些药丸有密切的关系,难道,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
林镇湘瞪大了眼睛,他一把扯下金久的上衣,把金久推倒在行军床上。
“你身上的毒是从哪里来的?这几天你一直在我的严密监控之下,根本没机会服毒,你也没有毒药可服。”林镇湘几乎绝望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刘仁把我带来的那天早上,我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了砒霜。我是祖传中医,对于药性有一种天才般的把握。我服用的剂量经过严格的计算,第二天早上才会发作,五天才会死掉。五天足够了,我可以完成所有的计划。现在才四天,我还可以活一天,我可以静静地回想我的一生,我可以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在心里听着君子竹的摇曳,伴着淮河的清风东去。”金久的声音低哑而平淡,就像在叙述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你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林镇湘颓废至极。
“是的,”金久说,“如果我有生的想法,我根本无法把药送到山上去。有的时候,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你不抱侥幸的时候,就会变得强大。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愿意用生命作一次令我自豪的尝试。”
“可是,你差点把你的女人搭进去了。”林镇湘张开了嘴巴,他担心自己会把牙关咬碎。
“我的女人只不过吃了一点苦,作为我的女人,那是她应该承受的,虽然我更希望她一点委屈都不经受。”金久笑了,想到了梅媛,他的心里感到温暖。
“但是,你不能因此否认我是个好男人。我把她牵扯进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前提是我能把她安全地送出去。”金久说,“我有过一个妻子,是我的助手,在那次刺杀你的行动中,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来到三淮城以后,我就下了决心,我要用缜密的心思为我身边的女人织一张网,让她们安全地活着,让她们过幸福的生活。”
金久想重新坐起来,挣扎了几下,终于放弃了。
林镇湘木然地坐着,连刘仁从帐篷外走进来都没有感觉到。
刘仁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看到林镇湘的样子,手伸了几下,还是缩了回去。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上峰对于刘千叶的突围非常恼火,措辞严厉地让林镇湘说明原因,听候处置。
林镇湘回想着几天来发生的事情,觉得自己正从头到脚慢慢地变成一堆草木灰,凉凉的,软软的,轻轻的,灰色的。他下意识地扭头看看刘仁。如果刘仁的呼吸重一些,会把他的身体吹得残破不全吗?
“旅长,不要再和他说了,一枪毙了算了。”刘仁掏出手枪,打开了保险。
林镇湘摇了摇头,他慢慢地伸出右手,把刘仁的手枪夺了下来,轻轻摩娑着。
“他还有一天时间,让他躺在这里好好思考人生吧!”林镇湘说。
林镇湘站起身来,把手枪插到刘仁上衣口袋里。
走到帐篷门口时,林镇湘停了下来,扭头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金久。
“你本来已经与他们脱离了,你已经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凭你的能力,还会有更美好的生活等着你。但是——南乡子,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林镇湘的声音虽然冷冷的,却因为困惑而发软,仿佛随时都会像雨丝一样跌落在地上。
金久慢慢地睁开眼睛,说,“你有信仰吗?你相信,信仰的力量吗?”
林镇湘愣了一下,脸色突然变得通红。他瞥了刘仁一眼,疾步走出了帐篷。
作家简介

孙志保,1966年生,安徽亳州人。198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亳州市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中长篇小说30余部,短篇小说多篇。其中,中篇小说《黑白道》《温柔一刀》《灰色鸟群》《父亲是座山》《麦子熟了》《葵花朵朵》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温柔一刀》同时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干事的日子》《奔月》被《中篇小说月报》转载;《飞龙在天》被《小说月报》转载。多部中篇被收入多种选集,如中篇小说《温柔一刀》被中国作协创研部编入《1998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长江文艺长版社)。著有中篇小说集《黑白道》,系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9-2000卷;长篇小说《黄花吟》。中篇小说《黑白道》获第三届安徽文学奖,中篇小说《温柔一刀》获第五届安徽文学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