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0-09-17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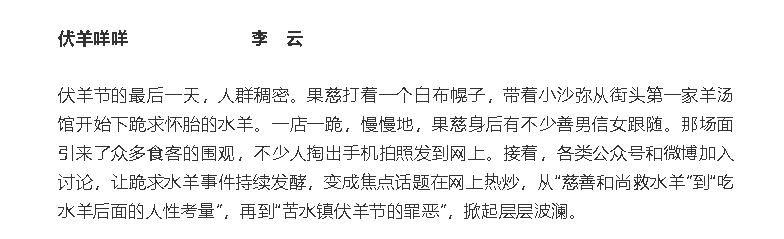
伏羊咩咩
李云
一
果慈走在去苦水寺的路上。
尚未入夏,不代表天气不热,还在暮春时节,天气就突然燠热起来。从远处看,通往苦水镇的省级公路如一截被人丢弃的猪大肠,乱糟糟的,好像爬满了苍蝇。近瞧那些蠕动的苍蝇是各色运货的车辆,以及行色匆匆的各色人等。车有三轮车、四轮车,甚至还有八轮车,自然还有皖北大地上常见的驴套车;人,只有三种:男人和女人,其余的,是僧人。
此时,僧人果慈戴着一顶斗笠,着一身杏黄色的僧衣,拖着有些疲惫的步子,坚定地向苦水寺方向跋涉。他没有向过往的车子招手,他一心要步行到那里,从九华山坐车到肃州县城他用去了四个小时,从县城去苦水寺,他又耗去了两个多小时,汗水在暑气和烈日的眷顾下,早洇湿了他的前胸后背,他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
在果慈的眼中,呼啸而过的车子,大多载的是羊,再不就是各种香料,羊有黑的、花的、土黄的,更多的是灰白的,羊们都睁大润起水烟的大眼,温良地看着一掠而过的村庄、田野和远坡的绿草,不叫不闹地一路向北,到那个苦水镇上去赴死。那香料是辣椒粉、八角粉、茴香粉,还有黄酒和生姜,如果和载羊的车不小心相撞,那就热闹了:惊慌的羊叫声、逮羊人的吆喝声、被香料刺激起的喷嚏声……让这截“猪大肠”瞬时像炸开了锅一般。
只是今天果慈没有遇见这般情景,他见到的只是不少朝苦水镇颠颠急走的流浪狗,流浪狗的基因里有去苦水镇赶美食节的记忆因子,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它们低着头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走得欢快而又十分小心,因为,专门有人会把它们用药毒了、用弩射了、电了、套了,或者扒了皮当羊肉卖。当然,果慈不知这些狗是在赶赴一个节日,它叫伏羊节。因为,他离开苦水镇已经有十五年了。
肃州苦水镇是胎记一样不容果慈轻易忘记的。阔别故土的日子,在江南九华山寮房里,他常常会想起皖北的小镇,常常会在梦里泪流满面,尤其是刚去九华山的日子,那时他才十岁。今天刚一踏上这块皖北大地,他就有了莫名的激动和悲伤。飞入耳际的鸟语、牛哞和侉腔侉调的乡音,让他激动得有些颤抖,他很想告诉行人和原野万物,“我回来了”,可他只能噤声,因为他已没有什么亲人可以倾诉,而且是个出家人,是释家的弟子,对于过去的家已不可再留恋了。老家那三间倒塌的土坯房,可能早就没有了。父亲是随村里人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阴雨天去城里卖血的,回村是高粱熟了的秋季,父亲和村人一样感染了艾滋病,这个病是灭村的魔咒,没用三年时间,就让这个村彻底取消了村名,剩下的儿童和老人被收养到孤儿院和敬老院,六岁的果慈分置到孤儿院。孤儿院不远处就是苦水寺,在一个早春清晨,八岁的果慈在寺里钟声的召唤下,拾级而上进了寺,从此,他有了师父慧普,也有了自己新的名字“果慈”,过去那个被乡亲们叫熟了的小名拾柴,扔在寺门外被乡野的风吹得无影无踪,如同那个曾经的村名——向阳郢一样,湮灭在平原大地的深处,无人问津。
果慈擦了擦满脸汗水和泪水,那些液体流到嘴里都是先咸后甜,他也弄不清楚是啥了,抬眼望向前方,心里盘算:再走上三里可过苦水河,过了河再走上二里就可到苦水镇,过镇上苦水岗北折五里就可到苦水寺了,忽然觉得路不再遥遥。近乡心怯,腿竟然没有力气了,他这才想起来今早到现在没进食,五脏庙唱颂饥经了。他看了手机,时间已过十二点半,过午不食,他只得一仰头喝了两口旅行杯里仅剩的茶水,清凉的茶水甘露一般洒向他干涸的喉嗓和心田,他告慰自己,到了寺里就可以喝上井水了。苦水寺里有一口甜水井,那是一口神奇的井。也许甜水井还在,可亲如父亲的师父慧普没了。
师父已在半年前往生了,圆寂之时,师父告诉身边两位弟子:“快让果慈回来接我的衣钵。”在慧普心中只有持大慈悲者才能当寺里的住持,果慈持有这样的慧根和心境。师父说完招手指向那个土陶钵,失神的眼中流出一行清泪,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向极乐世界远去了。果慈知道这个消息是两天前的事情,他刚闭关出来,不禁双手颤抖,双腿欲跪。消息来迟的缘由是苦水寺两个弟子都想当住持,秘不发丧,为了谁当住持两位同门弟子动了家伙大打出手,一位弟子被打成重伤,另一位逃遁到福建一个小庙里躲祸去了。十六岁小沙弥悟生把持不了苦水寺,就向肃州统战部、宗教局汇报,研究来研究去,只得依慧普遗嘱请回果慈。果慈匆忙收拾简单行囊,告别甘露寺同门僧侣和那伴他多年的松风淡云,一步一回首地下了山。
万绿丛中,一点杏黄如一只枯蝶飘飞归来。
二
大呆和小呆是一对夫妻。
大呆姓杲,杲字不好认,苦水镇上人偷懒,就叫他俩大呆和小呆。他们夫妻认为呆人自有呆福,没啥,就任人这样叫去,并脆生生答应着。他俩在苦水镇率先开了家羊汤馆,招牌字题写的行书是“呆家羊汤老馆”。招牌奇,店名好记,羊汤地道生意好。
丈夫大呆长得瘦削,四十刚出头,腰却有点弓,走起路来如鸭子一样,头一伸一伸的。媳妇小呆却很胖,个头又高,如女摔跤运动员一样,健硕的胖。
大呆烧羊肉是绝活,羊身上除了犄角、蹄壳、羊毛不能烧之外,别的物件就没有不能被烹调入盘成美味的。小呆白案功夫好,光是馍,她能做出二十多种花样来,菜盒子、饺子、饼等百多种面点,她都能轻松拿下。她揉的面好,两个油锤似的拳头在面盆里下了力气揉,面被揉得筋道,有嚼劲。
街面上混事的大毛看到小呆揉面,眼光就随着她那两只起起伏伏的大奶子变起色来,自然就会说荤话:“大嫂,大哥就是你每天在床上揉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小呆不恼,接话:“你不服赶晚上我来揉你,保管把你揉得三天下不了床,五天还得扶墙走。”
大毛就拱手:“俺服俺信,赶明儿个俺吃十个羊蛋后再让你揉吧!”
小呆一抬手摸了一柄刀,追过去就说:“俺现在就把你蛋骟了。”
大呆抽着烟嘿嘿地笑,六岁女儿风筝跑过来问:“爸,你腰直不起来真是俺妈揉坏的吗?”
惹来满堂哄笑。
呆家羊肉老馆的羊肉汤,那是真鲜,喝一口后嗓子都能鲜上三天,苦水镇就有一句谚语:“吃上呆家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
杲家开馆是十年前的事,周边江苏、安徽、河南刚开始过伏羊节,一进伏天,全国各地的食客都会赶集一样到那里去吃伏羊。那时大呆和小呆刚黏糊上,就牵着手到城里凑热闹,也下了汤馆,喝汤、吃肉、就馍……完了,两人就蹲在街角槐树的阴影下合计起来,小呆对大呆说:“那羊肉汤寡淡不地道。”大呆对小呆说:“对,那馍一点筋道都没有,赶不上俺爹做的。”说完大呆就吸烟抬头望天,小呆就用小树枝给一群蚂蚁搭一座过水沟的桥。半晌,两人眼里都一亮,仿佛灵光一现,就想出了回苦水镇开羊汤馆的主意。
“对,俺们回去也开个羊汤馆,不外出打工了。”
就这样,他俩在苦水镇开起第一家羊汤馆,这呆家羊肉汤馆就像酵母投在面团里,一下就发展成一个产业了。苦水镇现在有两百多家羊汤馆,连曾对此不屑的开煤矿的大毛,也在镇上开起了大毛老羊汤馆了,当然那也是因为他那煤矿违规生产被政府给封了,他也被关进看守所两个多月。大毛从看守所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抽起白粉,他两个儿子也都染上了抽白粉的瘾,见天的要打针。不能坐吃山空呀,他只得开汤馆了。
有了这几百家的羊汤馆,苦水镇政府的税收自然好起来,政府要把这产业做大,自然要办伏羊节,而且玩着花样向大规模办。于是,在皖北大地上,伏羊节就成了比过年还热闹的新节日。
这几天,大呆和二呆特别忙,忙啥,忙收羊。
他俩开车跑了四五天才收到一车羊,心急上火:一车羊三十只左右,只够伏羊节用一个星期的货,一个月没有百十只羊,就等着关门,那样的话,食客还不得摘了店牌子啊——因为,他家做的是回头客生意,去年就收客人的订金了。可是,今年这羊是出了奇地难买。
羊早被人收走了,过去上门送羊的情景已成绝版,现在汤馆老板都颠颠儿下乡上门买羊,羊成了比女人还要抢手的紧俏货了。他俩开车子跑了河南三个县的十多个乡,三天才收到这一车货,价格还挺贵的,更烦人的是各省各县之间都在搞封锁,羊不外运,查到外县外省的运羊车要卸羊下货,只给一点低价赔偿。他俩只好晚上赶路,到了皖北自己的地盘,才如长征队伍到陕北,终于松了口气。
驾驶室里,大呆睁着猩红的双眼,赤着上身在开车,小呆嘴不停地嘟囔着一些大呆认为的“废话”。
“×他娘的,明年俺自己养羊,老子不求人了。”
大呆不接话,心想,你这不废话吗?鬼让你要去买羊的,求人不就得看人家脸色。
“俺们专门养羊,肯定也能赚上开汤馆的收成,你说是不?”小呆问。
大呆还是不接话,心想,废话,养羊,你给它啥吃的?自家责任田早被政府征用建什么开发区了,让羊吃水泥地啃钢筋去,不是个心眼儿,乱说啥。
“要不是风筝的病需要大钱,我连馆子都不想开了,整天累得熊样。”小呆叹了口气。
大呆一听这话,就一脚踩上刹车板,对小呆横了一眼。小呆向前一冲,险些头撞到车玻璃上,便骂:“你发什么癔症!”大呆吼了她一句:“下去打点水,给车上羊爷爷们降温,不然都热死了,你就等着回去吃羊肉串,还不用烤的。”说完就趴在方向盘上睡起觉来。
每开上百十里路,就得停车给羊们补点水,可这快到家了,大呆却停了车。小呆下了车,风一吹,比闷坐在车里好多了。她拎着桶向河边走,一看这停的地方不妥,到苦水河了,这河水已脏得不能用了。小呆骂了一句,只能向田里去寻水了。
其实,小呆不是多话的人,她在车上喋喋不休地找大呆讲话,是怕大呆开车打瞌睡,把车开出点祸事来,她们家不能再出祸事了。
风筝是春天到淮北市医院,查出血液里有病的。六岁小公主竟得了这个病,小呆闹不清楚这个狗日的血液病病魔在皖北这地方为什么就赖着不走,前两年是艾滋病,现在是什么白血病。过去艾滋病是大人招的,现在这白血病却缠上了孩子,苦水镇已经有二十多个小孩得上这怪病了。有人说那是苦水镇的苦水河水被污染所致,也有人说是苦水镇上的人杀羊太多,羊神来报复了。所以,去苦水寺上香许愿的人多了起来。
小呆一想到宝贝女儿风筝就不由得流下眼泪,她用手擦着,用力地捏着鼻子,揪出一团鼻涕狠狠地扔在地上,仿佛丢了一团霉气。
大呆没有睡,望着小呆那胖胖的身影在烈日下向前移动。她穿一身印着红绿碎花的睡衣睡裤,风吹着,背影显得更加庞大而乱蓬。小呆嫁给他时,他的腰已在工地上受了伤,男人腰都直不起来了,在乡下还能找到老婆那是白日做梦。小呆却拼死拼活地嫁过来,让她爹打过,让她娘骂过,“好好的姑娘,怎么嫁给呆驼子,是欠他的吗?”她嫁过来后没少吃苦,刚把小摊子垒成二层楼的亮堂的汤馆,风筝却生了这怪病,又让她揪心了。大呆看着小呆的背影就知道她又在偷偷地抹泪了——她一哭就紧揪鼻子。大呆不忍再看,便闭上眼,一闭上眼,睡意就如潮水一样漫过来,他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
大呆和小呆都没想到这一次停车寻水会救了果慈的命。
三
小呆是在苦水河边看到中暑晕倒的果慈的。
果慈走近久违的苦水河时,被一股股腥臭味呛得快要窒息了,他扶着苦水河桥栏向下望去,那是一湾其色如墨、其臭如粪的黑水河床。河床上躺着一条黑色的巨蟒,慢慢地向前向下游蠕动着。黑色黏稠的水上浮着白色的羊皮和羊内脏,当然也夹杂着塑料袋之类的生活垃圾,这些漂浮物上爬满了苍蝇和蛆虫,那些内脏在烈日下膨胀并不时地发出“噼啪、噼啪”的破碎声。河岸上有几个孩童用石头砸着那些内脏,让它发出爆炸的声响,苍蝇们惊飞四散,又纷纷聚拢落下,在内脏上生卵成蛆,四散的还有孩童的嬉笑声。
“这还是苦水河吗?”
果慈睁大眼睛看着这风推动下缓缓移动如同出丧队伍的河水,不由惊诧地发问。
在果慈的记忆里,这河水清澈见底,河砂金黄,河水之上白鸟飞舞,渔船列列,渔歌阵阵,那时虽叫“苦水河”,但掬一捧河水可饮可漱。现在,这河水恶臭如腐尸,果慈干呕欲吐,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前途和来路,心里涌着酸涩。他朝桥头那棵大柳树走去,想去那里小憩一下,可刚落座,眼前一阵飞蚊,接着天地一黑,一头栽在柳树下。
小呆拎着桶走过果慈身边时,没有在意,只是心里想,这个和尚竟能在这臭水河边睡觉,看来不是高僧就是傻和尚。当她拎着一桶水再转回大柳树下时,发现这和尚有些不对劲,一群流浪狗围着他转,撕咬他的布包,和尚竟没有动静,并且姿势也不对,是脸朝下趴在地上的。小呆驱赶狗,弯下腰推了推和尚:“嗨,醒醒,别让狗吃了你。”
果慈没有声音,小呆把他推翻了身,才看到他那张惨白的脸上布满沙砾。这是一张瘦削的年轻人的脸,额头还有几粒青春痘,一双淡眉,双眼细长地卧在高耸的眉峰下,正紧闭着,高高的鼻梁下茸茸的胡须,嘴唇泛着紫色。
“了不得,这和尚八成是中暑了。”小呆一边紧张地向车子方向喊救人,一边掐果慈的人中,手忙脚乱地抄起桶里的凉水拍打和尚的前额和后颈。
小呆真怕和尚死在自己的怀里,出了人命可不是小事。“你醒醒,你醒醒!”小呆喊着用凉水朝果慈口中灌,可凉水又漫溢出来。
果慈恍惚听见小狗的叫声,这才从梦魇般的黑沉里挣扎醒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模糊不清的脸,一张胖胖的女人脸。自己刚才怎么了?是睡了一觉吗?显然不是,睡觉时会梦到师父,但这次没有。在一阵阵恶臭的提醒下,果慈意识到自己刚才中暑了,挣扎着坐起来。
小呆拍着胸脯说:“万幸、万幸,你终于活过来了,俺让你吓死了。”
果慈合掌行礼道:“阿弥陀佛!谢谢你救命之恩。”
小呆不好意思了,甩甩手上的水珠:“没啥,没啥,你醒来就好。”说完拎着桶又去打水,那桶水羊没吃到让果慈先用了。
小呆拎水再遇到果慈时,果慈神色恢复了生机,嘴唇不再是紫色,已泛起丹红,眸子不再迷蒙而有了亮泽,她对果慈说:“你这是要去哪?要不跟俺车子走一程,俺们去苦水镇,这天能热死人的。”
果慈答去苦水寺,小呆一听是去苦水寺,就问:“你是寺里的和尚?”果慈点点头,小呆就高兴地邀请果慈搭便车。她邀请和尚同行,是想带风筝去敬香求平安,她留了这个心眼儿。
果慈没有拒绝,随她一起走向车边。
小呆把一桶水倒在车上的两个脸盆里,羊儿们就围了过来,喝起水来。它们没有争抢,只是喝上几口就抬起头好奇地打量一下果慈和小呆,其中一只黑耳山羊还大着胆子走过来,用舌条舔了舔果慈那扶着车栏杆的手。果慈把手掌张开,任由它舔去,心里痒酥酥,如爬过一群蚂蚁。这时,果慈心田仿佛降下了一场秋雨,清凉且爽朗。他仔细注视着这只黑耳山羊,那长睫毛下的双眼闪着晶莹的光泽,如两颗玛瑙,眼仁流露着温柔和慈善的目光,如菩萨低垂的目语——果慈就是那会儿心仪上这群生灵的。
“上车,快上车,这天热得羊熊样!”大呆催着他们上车。小呆在果慈看羊时,已把他晕倒的事说给大呆听了。果慈上车时对大呆说:“麻烦你们了。”大呆瞥了一眼果慈,轰地发动车子,扔给他硬邦邦的一句:“你又不用我背,顺路事。”说完把车子开得如同有一百只狮子在撵一样,飞快地跑在苦水镇的省道上。
果慈被大呆呛得脸热起来。
小呆咕嘟一句:“你个驴日的……”好像在骂大呆。
驾驶室里一阵沉默。
过了片刻,果慈对小呆说话了,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说:“感谢你救了我一命,出家人也没有别的,我送你这串佛珠,愿佛保佑你们平安。”说完就褪下手腕上的手串。小呆晓得:这几年食客们不再戴拴狗的金链子,都戴这种佛珠手串了,听说有的手串比金链子要贵上几十倍,便推辞说:“我一个开汤馆的戴这个……”果慈说:“你不戴放在家里也好,这是开过光的,可避灾镇邪。”说完就把那串金丝楠木的佛珠手串递给小呆。小呆一听能避灾镇邪就满心的喜欢,咧嘴笑了笑,一转手就给大呆套上,并说:“谢谢!谢大师父。”
果慈笑了笑,合上眼睛。
大呆双目注视前方,僵硬的脸慢慢变得柔和起来。他觉得那串闪着金色的手串,戴在腕上竟有了一股凉意向全身传达,有种用深井水洗手的感觉。他觉得这手串有些神奇,心想,说不定这手串还能治好风筝的病,风筝从医院回家后一直靠吃药维系,没见好转,真是急死人了。
大呆突然一脚刹车,果慈惊醒睁开眼睛,打眼一看,前面路上有人拦车,一矮一高两个汉子打着手势,身旁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
“那是胡镇长的车子,他们肯定有啥事。”小呆猜测。
见车停,高个子小伙向车奔来,矮个子的汉子摇着纸扇子在树荫打凉。
高个子小伙隔着车窗说:“大呆,把我车拖一下,霉透了,抛锚了。”
“你说啥,我没听见。”大呆侧着耳朵问。
“我说车坏了,给我拖一下,你是真呆还是真聋了?”小伙子有点急眼。
大呆说:“我这会儿听清了,好吧。”
小伙子高兴地向自己的车跑去。
大呆把车子慢慢开到桑塔纳旁,眼看就要停下来时,突然加油变挡加速,轰一声绝尘而去。那个摇纸扇的汉子停下了扇风,愕然地立在那里。高个小伙子拾起一砖头砸向车后尘烟。
“哈哈,热死你个驴熊,鸟大孩子给镇长开个龟壳子,就不认人,叫我大呆,不叫叔我给你拖车,拖你娘的腿,哈哈。”大呆满脸兴奋,仿佛腰直起来。
“你个驴熊,你这事干的,八成要得罪胡镇长了。”小呆有些惶恐,就责怪起大呆来。
“怎么着吧,他镇长能咬我鸡巴还是咬我蛋,明说了我就是冲他来的。去年,他让大毛当了美食大王,让俺当了二王,凭什么,还不是大毛给他上礼了。”大呆把马脸又绷紧了。
“你就等着吧,今年你连三王都拿不到。”小呆转过头不理他,一侧脸看到果慈,有点尴尬,说了一句遮脸的话,“他就是没文化的犟种。”
果慈浅浅笑笑,一两句话工夫车子进镇了。
“师傅,我该下车了!”果慈说。
“忙啥呢,我把羊卸了,让他开车送你。”小呆忙说。
“不了,你们忙。”果慈坚持下了车。
“我会带我家女儿去到庙里烧香的。”小呆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
车停,僧下。
僧立,车走。
果慈移步向远处寺庙钟声走去。
蝉却无休止地叫着,伏天真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