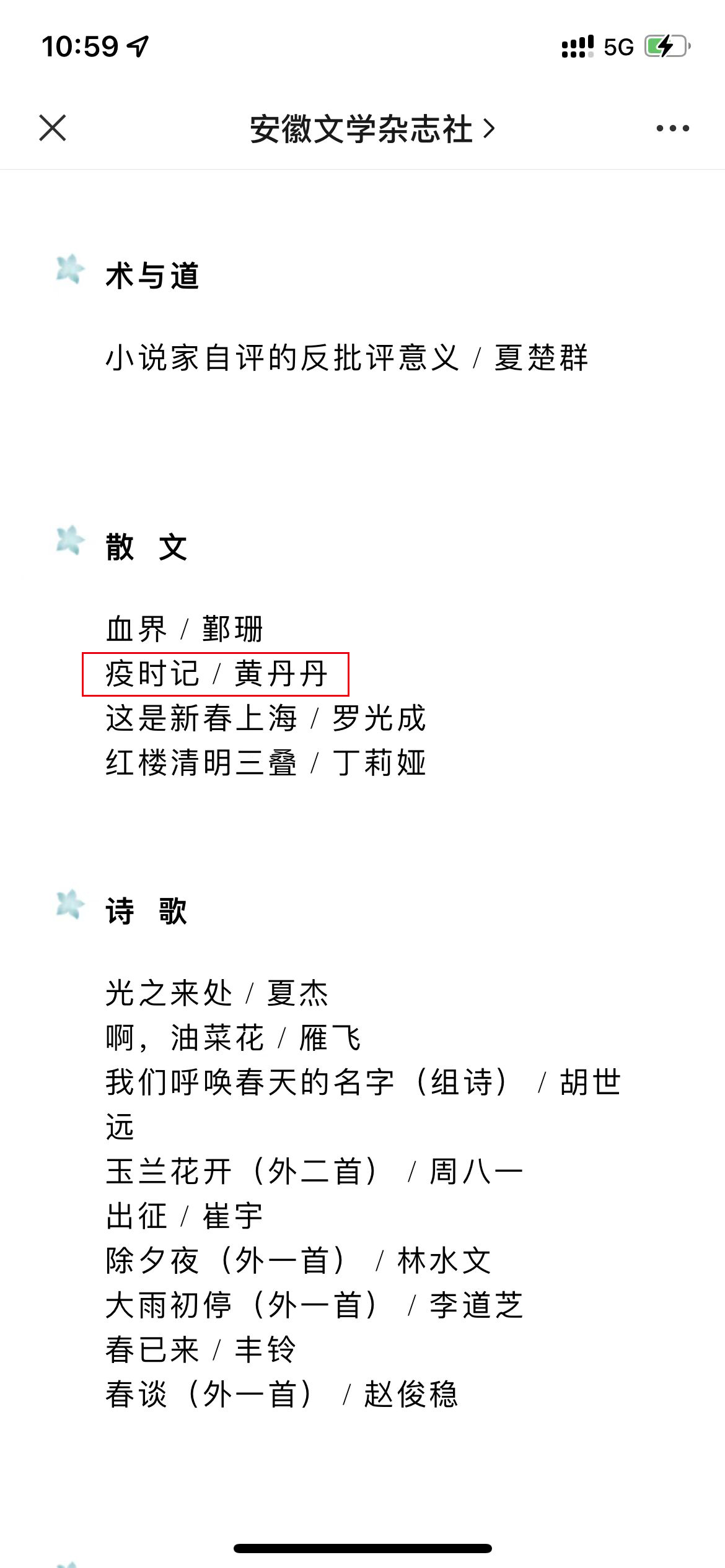作家黄丹丹近期作品频发:
短篇小说《故事里的人》刊《延河》下半月刊2022年3期;短篇小说《云山》刊《当代小说》2022年6期;
散文《疫时记》刊《安徽文学》2022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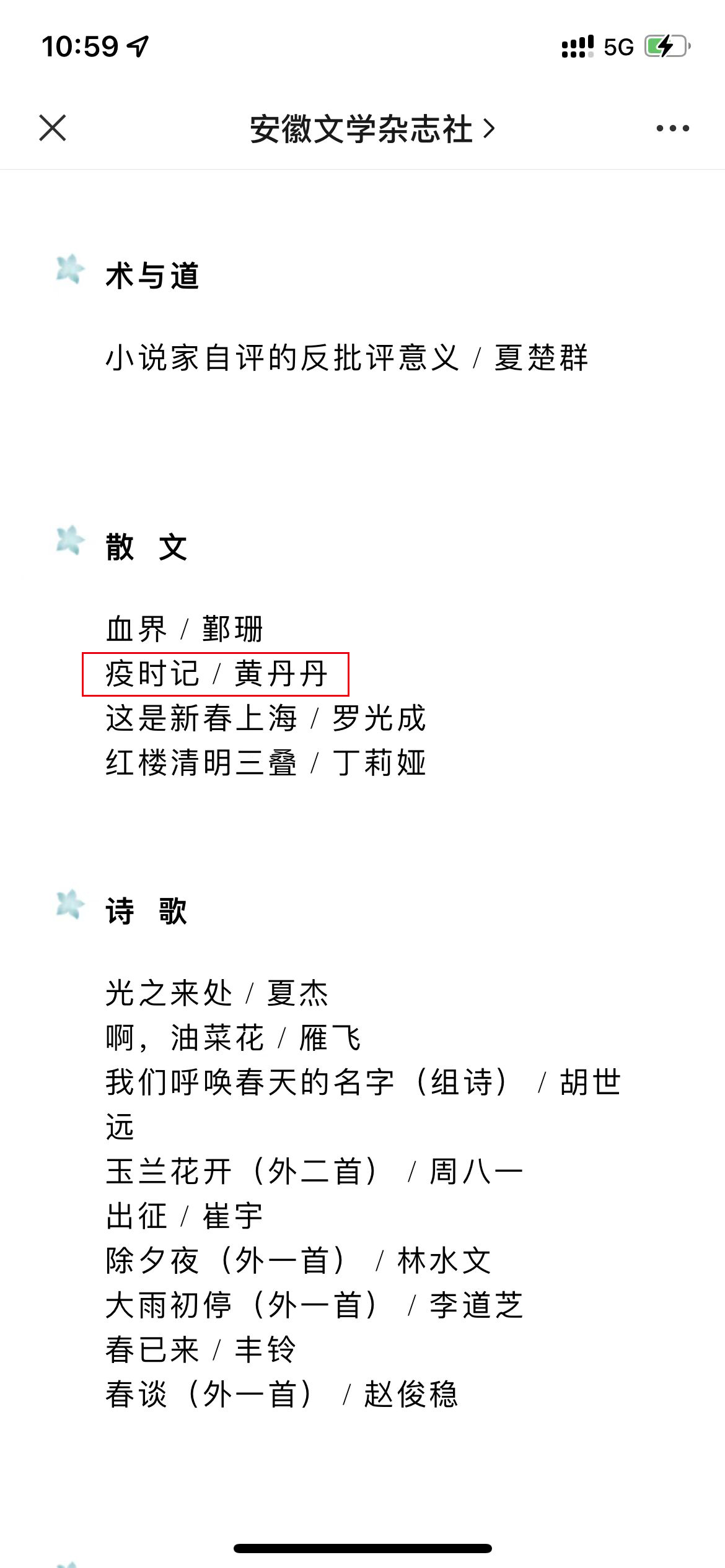
作品欣赏
云山
黄丹丹
曹晔听到那阵略显拖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门口止步,接下来,伴着窸窣声,一个烟熏嗓子“咳咳咳 ”地清了清喉咙后说:“开饭喽!”曹晔看了一眼手表,饭送得很准时,上午七点整。这是他隔离以来吃的第三顿早餐,这三顿早餐的开饭时间都精准在早七点。
曹晔应了一声,翻身下床。床是一米宽的木板床,一层薄薄的空调被上覆了一层硬硌硌的棉布床单,床单是新的,铺之前也没有过水洗一道。曹晔等那拖沓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才打开门,弯腰从门口的地上拿起一个袋口扎得紧紧的红色塑料袋。他关门进屋,把袋子放在床头柜上,不用打开看,他也知道,袋子里面装了两根油条、一个糍粑、一个茶叶蛋外加一碗盛在一次性塑料饭盒里的绿豆稀饭,也许稀饭里会有两块煮得稀烂的南瓜,也许没有。他打开塑料袋,果不其然,如他所料,只是稀饭里多了两枚煮得肿胀的红枣。
一天24小时窝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吃了睡,睡了吃,这待遇让每两天就值一个24小时班的曹晔感到奢侈得坐卧不安。这会儿,曹晔还不觉得饿,他把盛稀饭的饭盒盖子打开,将空调的风向调成上下扫风,这样,悬在床头的空调正好把凉风送到了床头柜上把这碗稀饭给吹凉。他起身,站在窗前,北窗外是开始抽穗的稻田,一块又一块绿色的稻田无声地延展成一片绿色海洋,晨风下,青绿的秧苗犹如身姿曼妙的舞者随着韵律摇摆,仿佛知道远处的那栋楼房的二楼窗口站着观景者——它们好久都没有被人如此欣赏了。曹晔出神地望着眼前那起起伏伏的绿色波浪,以及闪耀在绿波上的光斑。才早晨七点钟,阳光锐利的芒剑已经在四野里布下了刺眼的光阵。那些投射在叶片上的光斑点点相连,成了一面面对抗炙烤的金色盾牌,或一个个被光灼伤的金色疤痕。
空调突然发出“吱吱吱”的刺耳杂音,将曹晔的目光从窗外拉回来,空调出风口的挡板无力地震颤着,显出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他抬腿站到了床上,伸出他“长臂猿”似的长胳膊抬手轻轻把挡板往上一递,空调便乖乖地不吱声了。“哎,有劳啦!”曹晔对空调说,然而他并不确定这句话到底只是在心里想的,还是已说出了口。被隔离的这三天,曹晔感觉自己像个君王一般,独自占领了这栋有着六十个一模一样隔离房间的两层楼房,唯一与君王不同的是,他的身边没有簇拥他的臣子、奴仆与嫔妃。他是一个不统治任何人的君王,他占领一栋房子,拥有一方田野、田野上方他在窗内视力可及的天空,还有不时从他的窗口掠过的鸟雀、蜂蝶、蜻蜓、飞蛾,甚至,还有久违了的萤火虫。那晚起夜时,他无意望了一眼窗外,居然发现了一簇簇移动的光影,看了好一会儿,他才想到:萤火虫!同时,他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那么,刚才,他肯定也是把对空调讲的那句“有劳啦”说出了声。曹晔突然想到了爷爷,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他常听爷爷自言自语地说话。此刻,他才明白,人之所以会自言自语,是因为人没有说话的对象,自言自语恐怕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如果不这样,一个孤单的人的语言功能就会因为没有对话者而丧失。想到这儿,曹晔突然“嘿嘿”笑出了声,他笑自己也会因为无聊而胡思乱想。恐怕胡思乱想也是一种自保……想到这儿,曹晔摇摇头,决定不再继续自己的无聊联想了。他坐在床边,开始吃早餐。
刚吞下一个茶叶蛋,手机就在床头柜上震了起来。他抓起手机,看了一眼,是个陌生号码的来电,他按了接听键,一个女声,带有一丝犹疑地问:“请问是曹晔吗?”
“你哪位?”曹晔本能地以职业的警觉回问。
“我是隔离点的医务人员,今早你的体温测了吗?多少度?”女声听起来,显得略有些慌张。
“六点半时测了,正常的,三十六度五。你们换班了是吗?”曹晔说完后悔了,最后那个问句应该是留在心里的,结果被他脱口而出,显得他多饶舌似的。对方回了个“是”,又慌里慌张地道了声“再见”便匆匆挂了电话。
把手机放回原位后,曹晔继续自己的早餐。稀饭已经不烫了,温热的口感正适宜他大口去喝,虽然他希望面前有碗加辣的牛肉汤,但没有也就罢了,他只好认真地把稀饭喝了个底朝天。“浪费就是犯罪”——这句话已经被爷爷镌刻在他的心上,以至于他这个九零后的年轻人身上有着令人费解的俭朴。他用的还是五年前刚入警时换的那个手机,在那之前,他只用过两个手机,第一个手机是2003年到爷爷家之前,他妈用过的一只白色翻盖的TCL手机,他还记得妈妈收到爸爸送它这款手机时的模样:她披着齐肩的直发,穿着红色的毛线裙,把那个白色蓝宝石翻盖手机挂在胸前------那个手机上有条白色水晶珠子串成的链子。妈妈的面目已经模糊了。她已经走了快二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曹晔已经很少想起妈妈,并且想起她的时候,也不再像刚刚失去她时那般难过了。时间会给死亡的阴影蒙上纱衣,不仅如此,时间也会模糊活人的记忆。人们喜欢说时间如流水,是的,曹晔认可这种比喻,但他觉得时间也像泥沙,可以埋葬许多曾经鲜活的人、事与当时以为会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曹晔使用的第二个手机是他收到大学通知书向爷爷报喜时,爷爷揣着钱领他去街上的移动公司买的一款智能手机。曹晔还记得当他第一次在手机上登录了自己的QQ账号时的激动之情。那之前,他只能在偶尔去网吧上网时才能登录QQ,在她的对话框里写下大段大段的留言。她也是,家里没有电脑,且父母管教严格,不许她随便去网吧,只允许她在必需上网的时候,由大人领着去她爸办公室上网。咳,怎么又想到她了!曹晔将实在吃不下的半截油条放在敞开的塑料袋里——等小晌午时饿了吃,接着,他把一次性饭盒、蛋壳等丢进垃圾桶,然后开始准备给房间进行常规消毒。
就在曹晔进卫生间消毒时,急切的敲门声传进他警觉的双耳。他放下消毒剂,走出卫生间,冲着门,说了句:“你好!”门外传来因隔着口罩而有些瓮的声音,但曹晔还是听出来那是刚才打电话询问他体温的女声。她说,刚才打他电话他没有接,所以她直接上来了,他已经隔离了三天,按照规定,今天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请他开门配合。
曹晔打开门,把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医生让进了房间,然后按照她的要求,配合着她完成了核酸检测采样。曹晔正为刚才采样时遏制不住的恶心感到羞愧,在他以低头咳嗽来掩饰尴尬时,医生已经收拾好一切转身离去。曹晔惊异地发现,医生走起路来微跛地样子很像一个人。一个十几年前的同学,并且这里恰恰就是他们共同的母校!没错,这个隔离点正是曹晔就读过的向义中学,那时它是有着九个班级的乡村中学。
那天夜里被救护车送至这个隔离点的时候,曹晔就懵了,隔离点怎么会设在这儿?这不是他曾经度过一年不愉快时光的学校吗?得把时光往前追溯到2003年。那年的春学期,爸爸把曹晔送到乡下爷爷家,因为妈妈走了,爸爸一个人没法带他。“爷爷家就挨着学校的院墙,干脆去爷爷家读完初中再回城吧。”爸爸对曹晔说这话时,曹晔没吭声,算是默认了爸爸的决定。妈妈的去世让曹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长到十二岁,他的世界里几乎没有爸爸的身影,他脑海里全是妈妈:妈妈送他上学,接他放学,带他去游乐场,给他做好吃的……爸爸是个公务繁忙的警察,在家里常常缺席,偶尔见到他,他也总爱唬起脸让曹晔“把作业拿来我看看”,曹晔可不想跟着这样无趣又严厉的爸爸生活。那就去爷爷家好了,虽然爷爷家住农村,但爷爷总是笑眯眯地望着他,一口一个大孙子地唤他,每次见面,爷爷总要往他口袋里偷偷塞好多钱,还让他不要告诉他爸妈,曹晔买变形金刚花的都是爷爷给他的私房钱。
真到爷爷家住下来,曹晔才发现,爷爷家没有抽水马桶,上厕所要到又脏又臭的茅厕-----院子外,那间用碎砖砌了三面墙,搭了两块石棉瓦当顶,用蛇皮袋当门的小棚子。茅厕外观很寒酸,内环境就更别提了,曹晔伸头探脑地看过一眼:两块窄长的木板架在一口埋在地里的大缸上,那木板是供如厕的人踏在上面的,曹晔觉得自己压根没法稳当地在上面支撑住自己,于是他憋了三天没去大便,至于小便,作为男孩子,趁人不备就能在野地里解决了。爷爷发现他不肯上家里茅厕的秘密,便带他去一墙之隔的学校,虽然学校的公厕也是旱厕,但它至少比爷爷家的茅厕要敞亮得多。在爷爷家过了一个礼拜,直到学校开学,爸爸也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来爷爷家送他去上学,而是打来电话说,他正在外地抓罪犯,让他和爷爷一起去报名。爷爷带曹晔去学校找到教导主任,教导主任是爸爸的中学同学,他把曹晔领进了初一(1)班的教室。讲台上站着一位扎马尾辫的女老师,她环顾了一下教室,便喊了一个学生的名字,让他到后排去,然后安排曹晔坐在了那个男生的位置上。
在曹晔的记忆里,2003年的大事记上写着妈妈去世、转学和非典三件大事。印象中,开学没多久,学校就因为“非典”放假了。放假在爷爷家,每天守着家里那台只能收五个频道的电视机,新闻联播里每天都播放“非典”的死亡人数。曹晔想,那些死亡的名单里,一定有很多当妈妈的人,那么她们的孩子也和自己一样,成了一根可怜的草,“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那是妈妈教他唱的歌,每天晚上睡觉前想妈妈的时候,他都会一边悄悄流泪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唱这首歌。爸爸直到六一儿童节才赶来,带了一堆他并不爱吃的零食。令曹晔不开心的是,爸爸居然在上课的时候来到教室门口,不仅喊了他的小名“大宝”,还问老师王小亚是哪一个。
王小亚是个跛脚的女生,和刚才给他做核酸采样的医生有点儿像。曹晔现在想不起来当年他拼命和同学打架的具体原因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和王小亚有关。
住进来的前两天,曹晔就仔细地观察了这里的环境,并和记忆中2003年他曾读书的校园去对应。他一眼就认出自己住的这间房是当年初三(1)班的教室。王小亚要是在那所中学读下去,升到初三他就会坐在这间教室里。想到这,曹晔又像办案时寻找蛛丝马迹一般细致地察看墙壁,看了会儿,他不由笑出了声。都过了快二十年了,难不成这墙壁上还有当年那群混小子们写的“大宝和小丫是对好朋友”“小丫是大宝的新娘子”之类的大字?那群野孩子最爱给同学取外号了,曹晔因为爸爸在教室门口喊了他一声“大宝”,这个乳名就成了他的外号,而小丫则是王小亚的外号,来源是她的名字与当年一位很火的女主持人王小丫的名字谐音。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拿王小亚和他拉郎配,曹晔一直不得其解。因为他甚至没有和王小亚说过一句话,不仅他没和她说过话,估计全班男生都没能有幸听过她的声音,她在班里几乎是一个哑巴,就连老师的提问,她也不回答。但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甚至还有点残疾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成为“绯闻”女主角呢。一直以来,都是那些活动爱笑、生得好看、懂得打扮或有点特长的女生会成为众矢之的绯闻女主啊,直到现在,曹晔都不知道王小亚或者是他本人到底做了什么,让人误以为他们俩是一对儿。
好奇心一旦挑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曹晔希望医生就是王小亚。甚至,他已经确定了医生就是王小亚。他拿起手机,将刚才那个未接的电话回拨过去。“王医生你好!”说完,他就觉得自己有点阴险了,居然用上了刑侦手段。对方迟疑了一下,答:“你好,哪里不舒服吗?”顿时,他感到心跳加速,果然是她!
“没什么,就是感觉心跳得不大对劲,还有,嗓子有点不舒服。”他这也算是如实回答。
“之前有过心脏病史吗?家里有没有心脏病患者?嗓子不舒服先观察一下,可能与刚才采样有关。”
“我之前没有发现有心脏疾病,但我妈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猝死,三十多岁就走了。”曹晔说。手机陷入一阵沉默后,听筒里传来王医生迟疑的声音:“你是曹叔叔家的曹晔?”
“你是小丫,哦不,你是王小亚?”曹晔欣喜若狂。
“是的,你还记得我啊。曹叔叔他好吗?”
“当然记得你啦,咱俩不是同学么,还是一对好朋友,哈哈哈!”曹晔说罢感觉有点失礼了,赶忙紧接着回答她的问题,“我爸挺好的……哎,不好意思,我有个工作电话进来,先挂了哈!”
“谢天谢地!”曹晔想着,或者说着,同时接了同事的电话,挂了电话,他大声说了句“谢天谢地!”看来那一趟没白跑,这一次也没白隔离,不仅他之前参与的抓捕行动大获全胜,而且通过审讯,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了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
心情大好的曹晔,开心地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在那间由过去的教室三等分改建成的隔离房里兴奋得想跑、想跳、想唱,可惜,屋子里空间太小———就那么一间十平方的房间,
还在里面建了个整体卫生间,简直就像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曹晔对着窗口吼了几嗓子后,决定还是给王小亚打电话。刚才谢天谢地同事及时来电拯救了他,他可不想和别人谈他爸,难道告诉王小亚,他爸新娶了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吗?不知道的人都以为那是他曹晔的儿子呢。
王小亚仿佛盯着手机一直在等他打电话似的,曹晔刚按下呼叫键,听筒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曹晔掩不住得意地向她简单通报了自己取得的胜利,没想到她却没有回应。
“喂,信号不好吗?”曹晔自言自语地说。
电话断了。旋即又震。曹晔皱着眉,按了接听键:“儿子,好样的,没想到这案子在你手里给破了!”对那个激动的声音,曹晔只淡淡地说了句 “是大家的功劳。”就挂了线。他索性放下手机,站到窗前,看云。曹晔想起在他关注的一个公众号读过一篇写云的文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叫什么《云山》,通篇都在云里雾里地瞎扯,就像他此刻,什么都往一块联想,瞎想。
窗外的云,一朵挨一朵,渐渐堆积成了云山。不多时,凑成云山的云们又分裂成了云艇,两艘在蓝色大海里的游艇,没多久,云艇变形成了马群,马群幻化成了岛屿,岛屿演变成了雄狮……曹晔想,这变幻莫测的云,比他的变形金刚更多变。想起变形金刚的同时,曹晔想到了爷爷。当年,爷爷家就在这窗外,三间红砖房,一个空心砖砌墙围成的小院,院子里养着一群鸡,一条狗,一只猫,还有两只山羊。曹晔记得,当年,爷爷家屋后还有一条小河沟,沟沿边生着柳树。早春,柳树还没发青的时候,爷爷折下柳枝给他做了许多柳皮哨子,爷爷把柳皮哨子放在嘴里,变魔术般吹出了嘹亮的哨音。而他,无论爷爷怎么教,他始终没能吹响那些哨子。虽然吹哨没有成功,但他却记住了柳皮那青涩的味道。很多年后,他坐在护城河边等她的时候,心里就不时泛上那种柳皮般清新却苦涩的滋味。她终究没有去,爽约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今天。
从窗口望出去的那一片天幕上,如草原上的羊群般闲散的云朵们渐渐散成了云絮,丝丝缕缕地浮在天上,害得那蓝天就像是没掏掉口袋里的纸团,就放进洗衣机里漂洗后的毛衣似的,沾满了摘也摘不完的毛絮儿。曹晔穿过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外套,妈妈亲手织的,在爷爷家读书那会儿,期中考试,曹晔把用过的小抄团成纸团儿,装进了口袋,事后忘了掏出来。那件毛衣穿脏后,被爷爷丢进洗衣机里洗。那一洗,不仅把毛衣洗缩了,还把那件天蓝色的毛衣洗成了长满白毛的“毛衣”。望着那毛衣,听着爷爷的自责,曹晔心痛如绞。时隔多年如今,无论是想起妈妈还是爷爷,曹晔都已不再心痛。他站在窗前,任由自己在回忆里沦陷,逝者唯有在亲人的回忆里才能重活一遭。这几天,他感觉自己的心也沾满了回忆的毛絮儿,怎么摘也摘不净。
朝窗外望久了,曹晔甚至能从稻田里看见往事像蠓虫般朝眼前飞来。
在爷爷家的那一年,他学会了打架,最后居然一对二,把兄弟俩一个打破了头,一个打折了鼻梁骨……
手机的震动声驱赶了他眼前的“蠓虫”,是一通工作电话。琐碎的事情,他耐心地处理妥,挂了电话。手机在握,免不了又想到王小亚,刚才那一通非正常完结的通话,让他有点想再打通电话给她,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想和她说什么来着?哦,对,是他们揪出回一个潜逃二十年的罪犯。法网恢恢呀。曹晔的电话都回拨过去了,他又赶紧给掐了。他突然想起来,跟她聊这个不是很合适。
拖沓的脚步声与清理嗓子的咳嗽声像送餐前奏般响起的时候,又一个中午到来了。“吃饭咯!”依旧是那个哑嗓子在门口喊。
曹晔隔着门冲送饭的人道了谢。他猜那一定是位有关节炎的老人,少说也得有七十岁了。爷爷走的时候,也不过七十三岁,他歪着脑袋坐在一桌酒菜旁,被人发现的时候,身子已经僵冷了。那是四年前,爷爷刚搬进新宅的第一个中秋节。当年,爸爸得知曹晔打架被学校开除后,赶到爷爷家就对他拳打脚踢,爷爷恼了,砸断了一把椅子,操起一只椅子腿,就往打他大孙子的儿子身上抡……
曹晔吃完午饭,睡了个长长的午觉。醒来后,曹晔还久久不愿起身,因为在梦里他对爷爷的提问,还没有得到回答。
手机的震动,令他睁开了双眼。他歪着身,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过手机,一看又是陌生的来电。接通后,对方告知他,今天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曹晔道了谢后,又多问了一句:“你接王医生的班啦?”
“王医生?我们这没有王医生呀。”对方是个男医生,说罢就挂了线,把一个未说出口的问句憋在了曹晔心里。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午五点钟,曹晔测完体温后,立马拨了王小亚的号码,准备告知她自己的体温。可电话通了许久,却无人接听。曹晔只好回拨下午打告知他核酸检测结果的那个号码。对方很快地接了电话,曹晔报告了自己的体温后,唯恐他挂线,立马递上自己的疑问:“请问,上午给我做核酸检测的是不是王医生?”
“不是啊,她姓方。”
“她不叫王小亚吗?”曹晔不死心地追问。
“你听岔了吧?她叫方小亚。怎么了?她态度不好?你别计较,多担待些,她家里有事。”男医生说完又迅速地挂了。
方小亚?不对呀,她明明就叫王小亚,因为那时有个很有名的主持人王小丫,所以上学时那帮混小子才给她取了“小丫”这个外号。当年,曹晔之所以要发狠揍那对孪生兄弟,就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起哄喊:“大宝和小丫是好朋友,吼吼吼,大宝和小丫……”正在球场上掂排球的曹晔听到起哄后,立马举起球就朝起哄的那帮家伙砸过去,人群一哄而散,但那对孪生兄弟却仗着他们人多,其中一个拾起球就往曹晔身上砸,另一个则骂骂咧咧地说:“长臂猿配瘸腿狗!”曹晔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拳砸在他那张骂人臭嘴上方的鼻梁上。拿球砸人的那家伙,看自己兄弟被揍得鼻孔窜血,便朝曹晔扑去,曹晔被扑倒在地,也不知挨了对方几拳几脚后,伸出他的长臂,够到了一块碎砖,正骑在他身上发威的那小子,脑袋立马就被敲开了花。
这就是十几年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流血事件。曹晔断定,这栋隔离楼对面的那栋三层的楼房就立在当年滋事的球场上。当年球场旁有个工地,据说是希望工程捐款要建新的教学楼。没想到,当年被好几百号学生喧闹着的学校,只不过经历了十几年时间,就荒废至此了。不过,与荒废的校园相比,这个偏远的小镇倒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机场、高速公路、都市经济圈……都市化的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触角,悄悄地伸进了这里。曹晔入警后被分配到园区派出所工作时,爷爷比谁都高兴,因为移民迁建,政府赔给他一套带抽水马桶的电梯房,房子离曹晔工作的派出所不足五里地。他自言自语地说,老天有眼,当年亲手带大的大孙子,现在就在眼皮子底下了。只可惜,在眼皮子底下的大孙子也没能尽孝。曹晔一想到这里,心里便硌得慌。
王小亚的电话还是没人接。曹晔突然灵机一动,打开QQ。他飞快地从QQ的好友列表里找到“她”。她的备注名就叫“她”。曹晔至今仍清楚地记得,2006年8月31日,高二开学的前一天,他在网吧登录QQ时添加了她。那时她还不叫“她”,叫方糖。加了好友之后,曹晔还调皮地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咖啡”。也不记得都聊些什么,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总之,故事就落入了俗套——-俩人网恋了。设计情侣空间,使用情侣头像,彼此在QQ空间里给对方写情书……这段网恋持续了很多年。曹晔用爷爷送的智能手机登录QQ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她告白,并把她的备注改成“她”。对他的告白,她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曹晔回想,这段旷日持久的网恋,就跟那部没完没了的《猫和老鼠》似的。他一直在约她见面,她一直找理由不见。直到相识五年的那一天,她终于答应他在护城河边想见了,但,最终,她还是爽了约。从那之后,曹晔就下定决定,要从这张网里挣脱出来。为了戒断那虚妄的爱情,他甚至开始了戒网,直到现在,他使用网络社交平台的频率都极低。如今,像他这种不用抖音、不上B站、没有微博、不开微信朋友圈的九零后,可能是比“珍稀”还要高出一个段位的“濒临灭绝”了吧。他因此被同龄人视为异类,同时他也对那些整天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的同龄人感到不解与不屑。转眼间,他已到了而立之年。有时候他想,如果爷爷和妈妈都在世,他一定会被他们催婚。那么,他会选择怎样的女孩做妻子呢?玄的是,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他总会想到那个只留下一个模糊影子的王小亚,而不是和他在网络上聊了五年的“她”。这会儿,曹晔的突然脑洞大开地想到,“她”也许就是王小亚!
不要问为什么,曹晔说,做警察的破案也需要灵感,灵感来自日常的训练,也来自无法解释的第六感。而此刻,曹晔的灵感源于他对记忆的打捞与对细节的捕捉。
“她”黑着头像躺着曹晔寥寥无几的联系人列表里。点开她的空间,很好,空间依然是对他开放的状态,而不像他自己,早就将空间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而这些年,他也决绝地做到了没有再看她的空间。虽然她像一只不死鸟,不时地在他的心湖上空飞翔,但他什么也不做,逼着自己做到“心如止水”。
可是,点开她的空间后,他的心震颤了,一条条空间说说,一篇篇空间文章,外加相册里的照片,每一个字,每一帧图片,都印证了他的推测:“她”就是王小亚!“她”就是他一直想见,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才给他做过核酸检测的“方医生”!
电话突然的震动,让曹晔惊了一乍。看了一眼手机,他有些哆嗦地按了接听。电话里传来的女声也有些颤抖:“你终于进我空间了……”
曹晔说:“你终于现身了!”
她自顾自地说:“真没想到,二十年了,你们还能把那个恶魔抓回来!”接下来,她喋喋地说,曹晔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地由她去说,曹晔第一次发现,她的话语那么绵密,就像从泉眼般汩汩涌出的泉水,水流潺潺,激活了逝去的时间与模糊的往事,也解开了一些悬在曹晔心里一直无解的迷。
二十年前,曹晔的爸爸还在县刑警大队时,接手一个大案,涉及五条人命,毁了两个家庭。那是一起投毒杀人案。在向义镇那条凋敝的老街上,王、张两家近邻,在一个早上,毙命了五口人------王家夫妻俩和他们四岁的儿子,张家的主妇和六岁的儿子。这两户人家,留在世上的只有两口人:张家的男人和王家十岁的女儿小亚。当时口吐白沫的王小亚被送到医院,救了了一条命,但左腿却因为护士肌肉注射不当,伤了神经,造成了跛行。张家的男人不知所踪。
王小亚说,那些年,曹叔叔一直都在默默地资助她。曹晔转学到向义中学后,他每次去看曹晔的同时,都会给王小亚捎去很多东西,那几年,小亚的吃穿用度几乎都是他供的。几乎成了孤儿的小亚,在老街上,不仅没人同情,还遭人白眼。街坊们传言说,是她爸和张家女人成奸,才让张家男人发了疯,把他们两家人都灭掉的。两家人都快死光了,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还活着,不是扫帚星是什么?既然大人有这个态度,小孩子就学着大人,对小亚鄙夷得很。初一下学期,曹晔转学来,和小亚做了同桌。农村的小孩子,是很羡慕城里孩子曹晔的,但曹晔谁也不搭理,他只和自己玩。偶尔他爸来看他,让他带文具、糖果给小亚。他也不作声,只默默把东西放在小亚的课桌上。估计就因为这些,让那帮混小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编出了“绯闻”。
至于王小亚变成了“方小亚”,那是在在曹晔离开向义中学后发生的事儿了。向义中学教他们历史课的方老师,在那年夏天失去了独子。那孩子,其实都不能叫孩子了,他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放假回来,去游泳,溺死在校外的那条小河沟里。听到这儿,曹晔“哦”了一声,难怪窗外那条记忆中的小河沟不见了。小亚说,那条沟是被方老师一锹一锹填平的,原本小河沟也不大,不知怎地,就把那么个大活人给溺死了。后来,被方老师夫妇收养的王小亚,就改了“方”姓。
“所以,你给自己取了方糖这个网名。”过了好久,曹晔才插话道。
“是的,其实当初加你,也是偶然。不过我很快就知道‘咖啡’是你了。但我不想你知道我是我。”她嗫嚅着。
“为什么?”
“我,我不好看,我晦气,我……”
曹晔突然打断她,说:“你等着,等我隔离期满,就把你捉拿归案!”
说话间,电话突然断了,曹晔一看,手机黑屏,这老爷机,又罢工了。不过,这次突然关机并未令他烦恼。他心里安定得很,索性放下手机,站着窗边,望着窗口的那片天。天上的云,又堆成了山。那巍峨的云山,被夕光镶上了金边。突然,他听到,有脚步声清晰地透门传来。
作者简介

黄丹丹,安徽寿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第六届签约作家。发表作品百万字,有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字入选多种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