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2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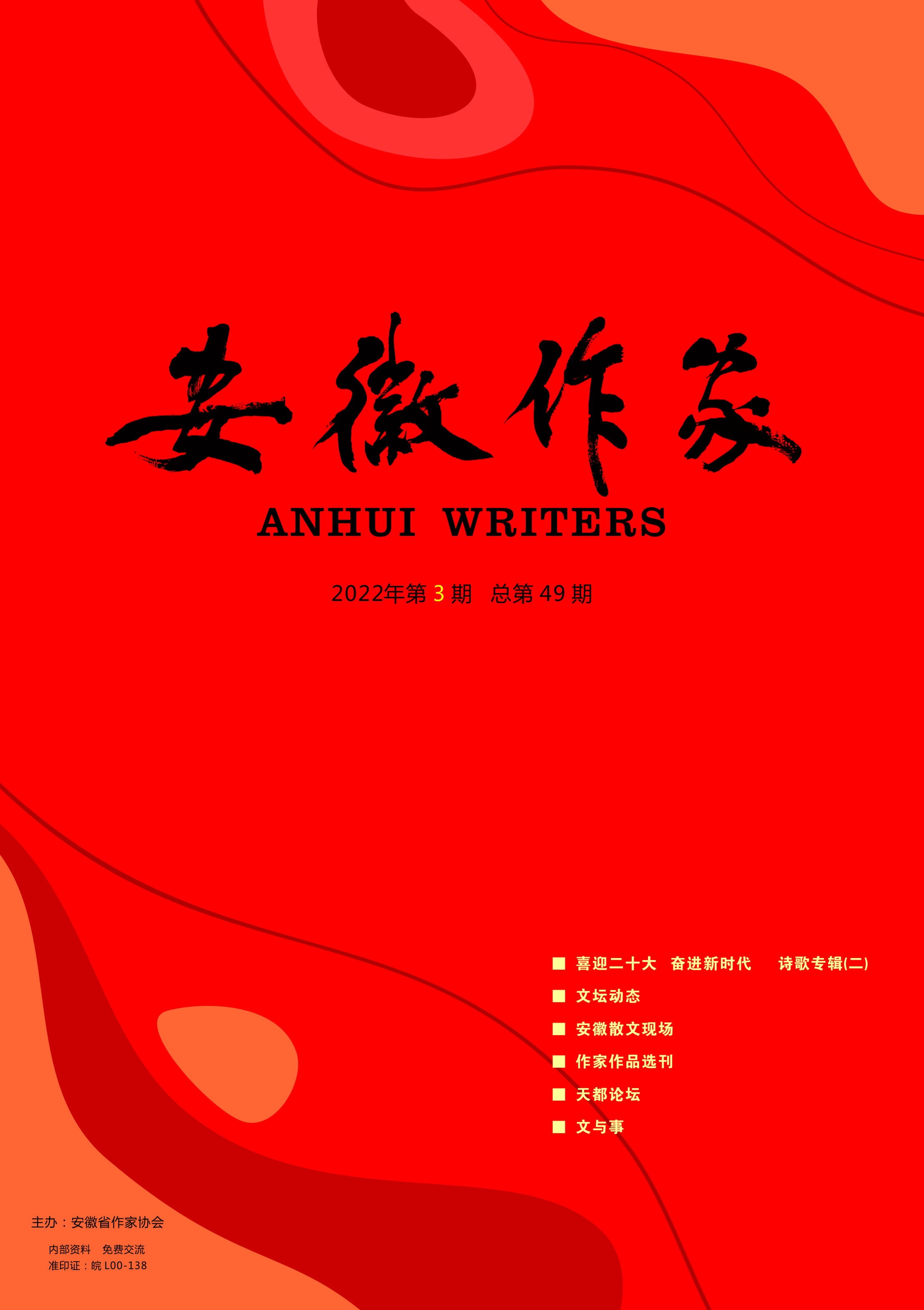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散文观:诸多文体中,小说,占了一个山头,绿树成荫;诗歌与戏剧,又分别占了一个山头,枝繁叶茂;山头与山头之余,是大片郁郁葱葱的草地,它们叫作散文。散文很大,它是文字最原始最茁壮,也是人心最辽阔自由的地带。
散文的魅力
赵 焰
说散文,是老话重提,也是重事重提。有些话,避不开,躲不掉,说千道万,也必须说。
仓颉最初造字,惊天地,泣鬼神。文字,那时候是用来通神的,文章自然也是。甲骨文不是文章,最早的散文集,应该是《尚书》,都是上古的文字,正大庄严,有万物有灵的意义。之后,青铜器出现,文字,也带有青铜般神圣的意味。先秦人作文,刀砍斧劈,铿锵有力,凡事都要说一个理来,列举寓言,也是说理。理直气壮,哪怕是歪理,也显得振振有词。那时凡文字成篇,皆是文章,由心而生,不玩词藻,不是“诗言志”,就是“思无邪”。《道德经》高蹈玄妙,神出鬼没,把世界的至理都讲透了;《论语》诚恳实在,雍容和顺,平易中可见性情;《庄子》恣意汪洋,风轻云淡,最可贵是难得的自由;《孟子》灵活善譬,多辞好辩,有凛然之威慑力;《韩非子》辞锋峻峭,雄奇猛烈,有强词夺理之急切。
先秦文章,如文字附诸甲骨、青铜之上,电光火石,意在不朽。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的,是《左传》和《国语》。据说左丘明眼睛出问题了,孜孜于《左传》;双目失明了,仍不放弃《国语》。左氏有力杀贼,无力回天,笔下的每一个方块字,都是刀剑淬火。不仅仅是左丘明,那时候的知识人,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兄弟等,都是以文字为金石,视文字为重器。他们落下文字,是以天地为鉴,想着石破天惊的千古之事。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文章,以此风格慢慢延续。后来,凡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的,都视之灵魂的祭奠,是用来封印的。文章,更被视为跟生命同质,甚至比生命更加永恒。
那时候的文章,最可贵的品质,在于真与朴,在于是非的坚守,以气节和热血激扬文字。字词落下,熠熠生辉,感天动地是作者的诚意。以真心作文章,文章不一定见真理;可是一定比假话作文要好,假话写出来的,一定不见真理。那个时代的文章,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先秦人写作,也遇到烦恼。烦恼是什么,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达不好把握,写着写着,偏离本来,或者言犹未尽,不敢多说。文章的游离和不确定,让人们更惧怕和敬畏,文字因此更生神性。人们不敢多说,也不敢多写;不敢乱说,也不敢乱写。
秦汉时期,文字如长城的砖石这样,沉重古朴。司马迁的《史记》,是其中的典范。《史记》就是无形的长城,黏合字词文章的,是无数的血和泪。若知司马迁对散文的态度,看看他那一篇千古雄文《报任安书》就知道了: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司马迁视自己惨遭宫刑为奇耻大辱,悲恸欲绝,欲哭无泪。《史记》,寄托了司马迁的生命,也延长了他的生命。司马迁唯个人良知为天理,宁死而不肯妥协。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惯例,只有帝皇才能列为“本纪”,可是修史的司马迁不买账,因崇敬项羽的英雄气概,将项羽列入了《本纪》系列,文字中不吝溢美,相反,对胜利者沛公,常有贬损。司马迁如此做,冒生死之大不韪,将一切置之度外。汉武帝想必十分恼火,却也无法,不好干涉太多,因为那时候的史志,尚不是官史,个人评藻中,尚有自由。
与《报任安书》一样铁血侠气的,还有李陵的《答苏武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这些文章的好,在于真意畅达,以热血为文字书写。箭镝破空,真意畅达,行文自然旷远;万千沟壑,聚云成雨,落笔自成文章。那时的社会,尚没有文人这种狭隘的职业。只有士,上马杀贼,下马作文;仗剑夜行,又能变身为行侠仗义的豪杰。
顾随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文章,都不是文人所写。好的文章,一定是情思哲思喷薄而出;也是“飞蛾投火”,不是烧没了,而是烧出生命的气息。好的文章之中,一定有一种大于文学的精气神作支撑,不是就事论事,或者单纯地叙述,而是以全部的生命能量,去拥抱作品,成就华美的篇章。
《离骚》伟大,是屈原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叹咏;《史记》伟大,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悲怆;后来杜诗的伟大,是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情怀。
汉朝出现汉赋这一种东西,华丽铺陈,可以视为文字的卖弄和游戏,也可以视作语言文字的技术拓展。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文辞,各有各的华美。可是华美过了,华而不实,就成为问题了。曹氏父子,是一个另类:曹操不是文人,他的风流高旷之气,让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曹操的好,在于有大性灵大胸襟大气魄大悲悯大境界,有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魏晋文章,曹操排第二,谁也不敢称第一。“三曹”当中,曹操排第一,曹丕排第二,曹植排第三。曹植才气第一,为什么作文第三?因为胸襟太小,文人气太盛。曹操的文章,曹丕的论文,兼有文采和性情,有大认知,都不是胸无韬略的文人可写就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视为“第二次百家争鸣”。外部文化传入,自我意识增强,产生了诸多有趣的灵魂。灵魂有趣,文章自然有趣。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可以看出魏晋之时知识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文章开头,是雅集呼朋唤友的轻松,可是写着写着,文字变得伤痛,沉郁而浩渺的悲伤出现了。这种悲情,不是传统的家国情怀,而是对人之为人本质的凄凉。王羲之的心境,比《观沧海》时的曹操更为孤独,也更为柔软。它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灵一层层地剥开,深入到最脆弱的内核了。
魏晋开始,本土的儒家和道家受佛家影响,生命意识觉醒,思维打开,聪明转为智慧,智慧连接虚空,转成艺术哲学。地理学著作,有张华的《博物志》、郦道元的《水经注》;医药方面,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葛洪的《抱朴子》;文论方面,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等。至于好文章,就更多了,除了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外,还有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宋书》、庾信的《枯树赋》等——这些文章,天朗地阔,荡气回肠,如秋雨后的蓝天白云。
一些志怪类文章也好,比如干宝的《搜神记》等,鲜活灵动,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想象力,体现自由意志,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延伸。
魏晋文章,真可以堪称高妙。这一个高妙,跟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有关,跟佛学的渗入有关。外来思想,激活中土,释放的能量有点超出人力范畴,随处都是鬼斧神工,随处都是余音三匝。
宗白华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句话,异常体贴到位,是今人对晋人的懂得。诸多魏晋名士的无情,有时候是深情,是对世界的深情,也是对人性的深情。
魏晋文章,还有音乐性——文字语言之间,有节奏变化的神韵,有内在的纹理,有数理的神妙。这些,都可以视为文字本身具有的神性,被发掘出来了。魏晋文章,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探索,它是以字词为手指,触摸神秘的领域。
魏晋南北朝之后是唐朝,唐朝有胡风,就文化上来说,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一路,有元气饱满、云开日出的浩荡,也有化繁为简的力量。唐初,诗歌是主流。唐诗,以废名的说法,是散文化的。唐诗,其实是韵文,不倾向于说理,而是情感的滥觞:一往情深,触景生情,情真意切,因情生韵,万物皆性,普天同情。到了中唐之后,韩愈实在看不过去了,这才站了出来,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提倡文章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将高飞的纸鸢,用线拴在手指上。文章因而变得更安全,也更踏实了。
与韩愈的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特点相比,另一个同时代大家柳宗元,走的是幽峭峻郁一路。他的文章,多是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结构精巧,语言轻灵,是唐宋文章中的另类。
“唐宋八大家”,是明初的总结和提倡,带有强烈的专制文化气息,对于旧时的“封神”。将天上飞翔的、地上奔跑的、悠闲旁观的文章,全都变成了正方步的标准。“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八人所作,当然是好文章,可也不能代表唐宋的全部,此提倡还是意在说理,意在策论,带有强烈的先秦风,此后基本被固定为中国文章的圭臬。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明清之风哪是先秦之风——先秦是“百家争鸣”的自由和探索;明清呢,是高压之下的雷同和桎梏。如此作为,早已南辕北辙,不是一回事了。
明清,制度“明儒暗法”标准,文章,也是“明儒暗法”标准。这一点不似书画——一直以来,书画相对超脱,评价标准,不是儒法,依旧是佛老。
八大家中,唯一带有佛老气质的,是苏东坡。苏东坡,堪称儒释道俗四位一体。他的《赤壁赋》,如拈花微笑、羚羊挂角。文章好就好在天地彻悟,有清风明月境界,以有限连接无限: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魏晋之后,中国文章大都端正肃穆,笔法精炼,大多时候,难得真谛,难得幽默,难入众妙之门。《赤壁赋》悟出了天地之道,也悟彻了人生之道,寥寥数百字,是大文章。《赤壁赋》的好,还给文章一个情感和哲思结合的示范,如洞开了一个大窗口,让人目睹了最大的可能。文章本身,有通透的彻亮,由于承载了大内容,文字也被激活,有了弦外之音;如玉石包浆,有了光泽,成为美玉。
宋文化,跟唐不一样,风格上清正风流、沉静安稳,接的是南朝的风格,相对雅致明理。唐宋文章,是拼命增加厚度,可是文章光有厚度不行,还得有高度和宽度,有灵性,有通孔。文章,当然可以格物致知,可是若隐去了头顶上的月明星稀,也摒除身边的滔滔江水,缺少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注入,肯定会变得呆滞沉闷,如死面团一样无法拿捏。
文学和艺术低劣的时代,很难说是好时代。元朝是这样,明朝前期也是这样。明代中期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有觉醒的愿望,有自由的意识,春意萌动之下,文学如春花沐雨,尽情开放。这一段历史,有文艺复兴般的意义,资本主义也好,人文精神也好,初具萌芽。相对自由的状态下,知识人个性十足,唐寅、李贽、董其昌、徐文长、金圣叹、李渔等,都是“奇谲”之才。人有了自我意识,性灵回归,自然活过来了,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文章有了性灵,也活过来了,融乐趣、情趣、风趣、志趣为一体,也是如花朵一样自在绽放。
文章跟人一样,需内外兼修。外在,是语言;内在,是情怀、学问、趣味和思想。晚明众多文人,寄情于山水和风物,文字中注入了生命意识,活力无限,生机勃发。晚明文章的好,最主要得益于人的解放——人性得到释放,有自由的心灵,文章自然而然就好了。好的文章,永远有着人体温度,甚至至情至性,是天地自然熏陶的结果,也是性灵悠游的一团雾气。
清军南下,国破家亡,大好的文艺局面也被毁。明末清初,傅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冒襄、张岱等人,既有国破山河在的孤愤,也有杜鹃啼血的伤痛。他们后来写出来的文章,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是千年的哀愁,也是千年的惆怅。
清代统治,钳制刚硬,“文字狱”的背景下,文章分为两派:一派为文选派,一派为桐城派。文选派以《昭明文选》为圭臬,讲究文采;桐城派呢,以承接传统为己任,讲究义理和文气,可是“义理”也好,“文气”也好,桎梏过多,拓展跟不上,气韵也接不上。义理追求,若难破禁区,下行为循规蹈矩;文气倡导,若没有自由,扭曲为装腔作势。桐城派名气和口气都很大,可是没有现代人文精神,文章生涩难懂,故作姿态,或者官腔陈调,或者陈词滥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连几篇像样的文章都找不到。
民国文章,重点在破,不在建。民国这个时代,承前接后,知识人有大使命,文章也好,文学也好,都是如此。以文章来破道统僵死的“神”,也破社会僵死的局,责任重大。
民国文章,是中西融会,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短短的民国,为什么出现了很多大师?是“旧学邃密”和“新学充沛”交融的结果——民国之初,全方位开放,东西方文化交流,几乎无障碍。优秀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做的又是不破不立的事,大气象自然形成,大格局自然养成,大师也纷然呈现。严复、胡适、林语堂等等,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激活的,是时势造大师,也是大师造时势。
陈独秀、胡适、鲁迅一干人,以文字揭竿而起,引导民众探索前方道路。路在何方,很多人不知道,若论清醒者,胡适绝对算一个。民国腔调的好,在于自由度,敢讲敢说,切中时弊,妄自菲薄。民国之初,各方面是很宽松的,言论相对自由,没有文字狱,没有精神桎梏,人们的创造力得到了激发,相比之前二百多年的严酷统治,最大程度上激活了社会的创造精神和自由精神。
民国文章,最精彩处,是真挚、高贵、尊严和趣味。最突出的,莫过于真挚。真挚,最基本的,是讲真话。文章,最可贵的,还是“真”吧,一“真”遮百丑,一“假”毁百优。以真为基础,讲真话,说人话,是做人做文最重要的东西。真话,不一定是真理,可是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真话,有美的光泽。假话,没有美的光泽,只有铜锈的青绿,泛着难看的死色。
文章之背后,实是人心,是思想的突破,以及意志的艰难前行。人心软弱,难成黄钟大吕。
真挚、高贵、尊严和趣味,这四个词后来为什么屡屡让人缅怀,是因为中国历史上,能体现这四点的时代,是少而又少。
民国历史太短,万象伊始,尚未深入,就已结束。民国文章也是这样,若论深厚,暂且不足;若论广博,也嫌不够。民国以文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论在现代汉语的确立,还是时代精神的探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文学单骑突进,文化没有系统改造,国民性整体没有跟进。到了最后,不免雷声大雨点小,声嘶力竭中,性命孱弱,最终还是坍塌下来。
民国,破了文化的“神”,也破了文章的“神”。文章破“神”之后怎么办?有的堕落下行,沦为工具;有的依旧坚守,寻找新的神灵。民国白话文,尚未从古典文字中走出来,思想尚未成熟,精神尚未深入。不过那一段时间的文章认识格外纯真,表达极有诚意,好似当时女大学生所穿的白衣蓝裙,清纯是清纯,积极归积极,却有些呆板,难得有老道圆熟的认知和智慧。
试着总结一下:先秦文章,有思想,有力量,有风骨;魏晋文章,有真谛,有才华,有趣味,有风云气象。唐宋文章,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之后,文章写着写着,格局越来越小,横里也变小,竖里也变小;横的是文采,竖的是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章,强在形式,强在音韵,强在风华……弱在思想,弱在哲思,弱在幽默……文字与思想,一直是血肉和筋骨的关系,概念上是可以分割的,事实上却是无法分割的。好的文章,一定内在带动外在,以性灵和思想带动语言文字,绽放出迷人的自由光华,蕴藏着对众生的安抚和拯救,并以与社会的连接,点亮精神的闪光点。
文字,若能够找到与天地、自然、社会与人心的连接,不断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好文字;若以文字的功效,不断地探索世界的本质,也是足够光彩的好文字。
以我的认知,散文,或是思想的光华;或是文字的魅力;或是意志的前行;或是情趣的表达;或是禅意的隐约……好的散文,一定是生气勃勃的:它是清风明月;是葳蕤生长的植物;是田野氤氲的岚烟;是柔情摇曳的花朵;是夏夜小河边的萤火闪烁;更是头顶上璀璨无比的星辰河汉……文章,还是清妙的福音,如“奇异恩典”般的歌唱,有自上而下的恩泽和光亮。以我的观点,《圣经》也好,佛经也好,都是最美的文章。那种文字中蕴藏的般若性,那种腔调中的善意,那种虔诚的态度,那种圆融芳香的气息,那种清静恍惚的圣洁,都是叙述和表达的绝美体现。如此文字,字里行间,静谧空灵,仙乐飘飘,有内在的韵味,有永恒的诗意。相反,那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无病生吟的东西,都不能称之为好文章。
强调一下,稳固常识——散文如花,花朵呈现的光泽中,一定要是真的,唯“真”才是生命。“真”是通灵的,是“善”与“美”的基础。没有“真”,不是“善”也不是“美”,只是如塑料花一样漂亮,也如塑料花一样虚假。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文采,是外在的;质,是内里,是内在的。此语可以形容君子,也可以说文章——好文章,也是“文质彬彬”,其美如玉。顾随说:“中国文学、艺术、道德、哲学——最高境界是玉润珠圆。”这一个标准,是通感,也是天道,是客观存在。好的散文,浑然天成,如同美玉,那一抹无比迷人的润泽,是天地之灵光,也是迷人的人情之美。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赵焰,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曾在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发表作品500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异瞳》《彼岸》《无常》,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历史传记《晚清民国四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晚清之后是民国》),文化散文集《思想徽州》《行走新安江》《千年徽州梦》《风掠过淮河长江》,电影随笔集《人性边缘的忧伤》,散文集《此生彼爱野狐禅》等30多种。《宣纸之美》入围2021年“中国好书”70强。安徽文艺社已推出“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赵焰文集卷二:散文随笔精编”“赵焰文集卷三:长篇小说精编”。
作品欣赏
散文观:万物有灵,通贯古今。散文里当有自在本心,自由本原,自我本性。风起于青萍之末,散文是“起”之势,是风起之前的酝酿。无所谓大,无所谓小,大大小小,均是散文本色。
皖人歌
黄亚明
宵夜帖
乡村秋夜,如墨水洇开,偶尔见光。闻虫声如织如雨,如玉米林里万籁流走,如梦如幻如棋中的匹马爬岭过岗。草窠里,叫乖子(雄蝈蝈)像羞怯的男孩,一声促短,一声吟长,类似当年祖母纺织时的“唧”“唧唧”“唧唧”,岁月的金梭银梭啊在织一匹梦的土布。间或停歇下,旋即复起。夜露深重,各种虫声近在眼前,却不知其所在,其所终。古人说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将入我床下。九月的乡村之夜,远看近看山色乃天色所化,混沌一块,墨色一片,黑暗深处却似藏有锦绣一团。我想起往日田野,稻茬约莫一寸高,风吹来,刮起干枯的草衣,连渐渐升起的黄月亮一起窸窸窣窣。今夜月亮的黄铜锅子,沸起草木香、泥土腥气、缓落的秋露和牛羊鼾声以及一大群不知名的静极的声息。四野阔大,一团锦绣是奶油似的黄月亮,升起在东山。万物交会的一刻,我像大地的孩子贪婪注视:今夜月亮的黄铜锅子,掉进了土灶旁的大水缸,清水晃荡,它在孤独地舀啊舀,舀啊舀……
石佛寺记
山深藏老寺:石佛寺。大别山南麓,皖西南,隶属包家乡。周遭云横雾漫,山川清凉。石佛一词,空灵寂静,如叶落空山,又如木鱼“笃”、“笃”、“笃笃”,昼夜不止。石佛寺读来则如嵌在峭壁上的楚音,清癯苍冷,荒疏枯涩。黄昏的山风吹来,吹开偏居一隅的寺门,一阵阵的冷,又有繁华将逝、明灭变幻的空茫。
春日的石佛寺外,却满眼繁花的喧闹。一山绿,绿中掺红,一山新叶老枝,一山夕辉,一山芳菲,荡荡春色如水,没心没肺。简陋的寺门内,荒废破败,三尊旧迹斑斑的大石佛,数十尊小石佛,油漆剥落,外用木板护体,石不像石,佛不像佛。数块碑刻,字迹模糊,其中一块疑似提示道光年间重修。石佛更不见乾隆三十一年初建时的金碧辉映,金碧也是逐溪流鸟声深红浅绿而去。唯岸边三两桃枝渥然似托举旧梦,开得人眼热心跳。
溪水间游鱼历历,鹅卵石一块块,倒映天上白云的无量吞吐。
世事如家常,石佛寺是极简叙事。
寺边右首有古松,虬枝凌然、凛冽。古寺,古松,在天地间各自像一片微小的绿影,被古僧扫进了夕阳的群山之中,一时寂然。一时出神,神飞四野八极。
石佛寺产茶,产佛茶,产神茶,产仙茶。海拔八百米以上的茶山绵延数百亩,一大片绿,一大片绿,铺天盖地仿佛幻觉在沉静堆积,风一吹,并未有丝毫摇动,只是使绿意变得越发强烈、浓郁:石佛的绿影,新老叶片的绿影,茶姑的绿影,采茶竹篮的绿影,路边小狗的绿影,白墙黑瓦的绿影,光阴的绿影,亮亮水泥村道的绿影,整座山中乡镇的绿影……
石佛有颓唐之美,破败之美。诸神用神来之笔,种神来之茶。神佛之绿有仙气。寺边一棵母茶树,被乡民目为神茶,半边是长椭圆形叶片,茶味普通,另半边是柳叶形叶片,茶味绚烂,所谓大别山中“半棵神茶"。茶宜做半神,人宜做半仙,肉身沉重,食得烟火味,便是笑口弥勒。
东汉壶居士《食忌》载:“苦茶久食羽化。”所谓日曝夜露,便一叶羽化,百叶登仙。山中风月滋养,水落石出,遂神气阗溢。
茶树名石佛翠,石佛翠滴翠,静气盎然。所制茶名岳西翠兰,略苦旋甘,清香似暮春草木入怀,又如奶油炒米,抚慰饥肠和风尘。
我喝了一口纯正的翠兰茶,心中像覆了一片民间的青瓦。
手工翠兰茶,到顶级便是翠尖,一芽独立,骄傲、蓬勃、烂漫、严谨,老手工都是岁月的知己。翠尖的手工,来自老茶人冯立彬,几十年默守山里事茶,种茶、育茶、采茶、制茶。又独创翠螺形翠兰茶,手心一捧,如无数翠绿法螺横陈春野,鼓荡一鸣千山振。这一切的好,全好在天性。民间小寺和山水,留下真善仁义信的天性印迹,瓜瓞绵绵。
石佛寺不大,石佛寺很大,芥子中藏须弥。山到高处即为仙,潜藏白鹤、溪水、游云、羞涩和爱,杉木和松柏都怀着古人的赞美,心中都住着清风。
正是清明之后不久,天气清明,万物晴正,山似一棵石佛翠,水似一汪碧螺春。
入夜饭饱,辞冯立彬而去。他眉眼内敛,暮色里垂手而立,像极了清寂的佛陀。
虎形记
虎形的油菜花开得略带浪荡,山田中去年的稻茬约莫半尺深,枯败而色泽灰白,不经意田土上竟冒出一层层小绿。绿意是很淡,却有几分绵绵,绵绵不绝。许是前几日冷湿下了雨,又或是上头挖机在给新建的民宿挖土,溪流涨大了些,微有混浊。溪边不远处的洗衣妇在捣衣。这是难得一见的古景色,如今几乎也没人在河畔捣衣了。捣衣只在山里,或者南方之南(江南?),纯净的山水和老画中。也没什么遗憾,前尘而已。溪边坐一个钓客,纹丝不动,似乎自己就是肉质的钓竿。他身边三三两两红男绿女,在一堆卵石上撒欢。呆久了,钓客偶尔动动身子,溪水似乎也颤抖了一下,一条溪就被这些人弄活了。山里就是这样,晨昏寂寂,不知其所来,不知其所终。来时我经过新结对户王业华家,是第一次见面,自报家门,他热情地散烟。这是个精干爽朗的老人,儿子在浙江丽水做项目经理。以前承包过车队。我们边抽烟边闲扯,小楼房在我和他背后,门前有葱蒜之气,一畦畦溢出来。然后我往更深的山里走,去结对户杨全友家。靠山,很高的山,费劲抬头看最上面是老树,各门各类,也叫不出名字。之后是悬崖,特陡峭。再下面有好几畦菜地、茶园,山脚,田堤边角,摆放了几十箱子土蜜蜂,几万只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嗡,金晃晃,并不觉得可怕。真是好天,天色很蓝,哪家的牛哞了几声,河对面人家的电锯似乎在咬啮松木,呼哧呼哧,松香被阳光弹到了天空。电锯声像一排排五线谱,那些下乡搞批发送货的车子,那些防疫值守时看抖音的妇女,那位目不斜视读报纸的颇为骄傲的杂货店主,以及,摩托车、电动车、黑色白色红色轿车,间或有从村部探头出来的村民,乳娃的啼哭,都像五线谱上守规矩或者捣蛋跑调的音符……现在我站在村部大门口,正对着“某某婚庆”背后的大山。不见山色,只见漫山竹色青黄,无风自动,有风也动……
公园记
春绿已深,春红也深了几层。淝河公园里,树树的影子参差静默,透出的绿阴洒在人脸上、人身上,清凉中有薄暖。一路行去,早晨的野气渐渐磅礴,在林深处,鸟叫得十分动荡:从一棵树蹦到另一棵树,从一根枝条蹦到另一根枝条,似乎她们天然拥有湿亮的嘴唇,琴弦般的腰肢,随便就甩出蜜色流光的音乐。已忘了什么树,高大清瘦,细枝长条,隐含一种南方岁月的清啭之美。鸟叫声盘旋,波伏回环,风情张扬。我静下来,草木的生气包抄过来,萌动中绿光烁烁,青葱闪闪,仿佛身体里簌簌作响,积尘抖落,解脱了一些凡俗琐事,心中养了一座园子,一座野肥垂滴的绿国。
我观察过小坡上的四籽野豌豆,绵绵密密,卷须忐忑轻摇,采采卷耳的稚嫩样子。尚未结籽,花色清癯的紫白,旗瓣长圆,翼瓣椭圆,娇弱小小得似要涌出雌性的腥甜。识花君云,四籽野豌豆可治疔疮、痈疽、发背、痔疮、头晕耳鸣,兼明目。明人鲍山《野菜博录》记载,苏地称其为鸟喙豆,又名丝翘翘,极为象形雀跃。其幼苗入馔,滋味清逸。经氽烫,清水浸泡,炒食、凉拌、做汤均好。白瓷盘上清白盎然,有沧海桑田、破而后立的一份生鲜。最喜欢雕版的《野菜博录》,白描插图,洁净素雅,扑面一派野蔬气,洗人肝肠。
园里的大岛樱散布各处,高耸亭亭。我来时,瓣色已是红白交杂,瘦白萎红,流露一种绚烂后的疲惫和宁静。樱花期短,盛开时如川端康成笔下《伊豆的舞女》,一片纯白,羞涩、天真、清纯、童心未泯,慢慢,胭脂红,慢慢,哀愁淡淡白白。想起佛家的苦禅,大岛樱也是修行,花开是花的风流,花谢是花的必然,短短暂暂,用情至深,待到结籽,籽也是青秀,小小团团,青秀到几乎无籽。关于樱花,日人小林一茶有俳句,其味绵长。小林一茶一生冷暖深痛,语意多慈悲:
黄昏的樱花,
今天也已经变作往昔了。
今天在明天是往昔,明天在后天是往昔,昨天在今天是往昔。不看往昔,只看今日。人总要往前看,看到一团锦绣,看到云淡风轻,大抵的况味如此。
园中灌木矮矮,扇骨木的身姿像一大蓬绿雪,叶丛浓密。再过三两个月,至六七月间,当是白花簇簇如雪团,如白浪翻涌。高大挺拔的青钱柳,与阳光接壤,叶多,色绿,清香散逸。海棠花开得艳,粉红、纯白的重瓣堆如锦绣,若与玉兰、牡丹、桂花相邻,满心的玉堂富贵。苏轼怜惜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大胡子苏轼从来豪放如喷泉,他梦中的加油站却有着涟漪的美,俨然小家碧玉,柴门悄立,绰约有姿。这种美,往往夹杂着一点挑逗的危险,更触动人的侵略性。张爱玲憾恨海棠无香,无香却有了不染尘的入髓,层层叠叠。其果质朴,小而酸酸,酸而甜甜,甜则在啖口的余味里绵长。想到凡事不可满,不可溢,不可全,不可尽,令人一时通脱。
也喜欢红花檵木,奇异地结合着绸带一样的红色光晕,风致劲浓,红紫跳脱,恍如急促的心跳。也喜欢翠柏、六道木、雄黄兰、小叶椴、红叶卫矛,赤橙黄绿,喷薄出强悍的少年之气。少年之气,多得了兵家纵横气,万类萌生的酒意,意气相契。人到中年,愿少年气多些,正大晴朗。
有事没事时,都要到荷塘边坐坐。是荷残,枯枝交错,弯弯折折,荷影和蓝天倒影交互,残叶莲蓬卷缩,难辨形体,似无意泼散的黑块与黑线,虚虚实实。曲线直线纷繁穿插,水上水下难分。微风轻摇,残荷如水袖,带出舞蹈的节奏,尤为别致。几位老人坐在斜坡上看荷塘,洒下一片混沌的安静,也可以入画。
八大山人画荷,铜驼之悲、愤世之慨,连墨鸟亦啼不住。吴冠中画荷,几茎墨立,风神入骨,溢于楮墨。任伯年画荷,清新温雅,游禽嬉乐,是杨柳青的喜悦。
园子上方,有两条高铁线,每隔十来分钟,呼呼呼的声音一阵流淌……东来西往的高铁,乳白长龙,呼啸而过。
树下,花下,凉亭中,红男绿女渐渐缤纷,契老携幼,交头并立,自有快活。
从我家新居到园里,二三十米。从园里到我家新居,三二十米。闲闲散散,闲散走数十步,便是我的园子。
日色赤金,一切安吉。
这一天是3月24日,新居入住。花开富贵,吉屋见喜。
叫了三五声
香椿两棵。棕树三棵。四季青两棵。石榴一棵,大红(籽)朵朵。数错了,香椿是三棵。另有枇杷一棵,五月结子初黄。初黄是好颜色。亦喜欢结子二字,情爱贯底,枇杷子在天地间也是芥子。芥子须弥,因为心情骀荡,芥子成了须弥,枇杷子在密叶间砰地爆出,一院晴和。
忽然来了一只鸟。鸟不知名,多叫了三五声。“唧呦”,“唧呦”,“唧呦”,“唧——呦——”。
单位院落内很小,有枇杷子已足,何须石榴、香椿、棕树、四季青。或许需要石榴。石榴花好,好到天地艳阔,令人心境朗然。香椿我素来不爱吃,爱物不一定爱吃,据说初芽的香椿汆烫后,青碧不改,香气浓郁,是为春天第一鲜,最得食客心爱。
说说枇杷。民谣曰:枇杷枇杷,隔年开花,囡儿要吃,明年蚕罢。
方寸间,乡野之气兜头一扑。
又有《盘解歌》,云:
随在一,唱在一,唱在腊,解在腊,什么开花在水里?枇杷开花齐刷刷。
儿歌多无意义,但记得枇杷开花有白有黄,其上偎以绣眼鸟,裁画下来可做玲珑扇面,素朴而忘魂。
亦可以老杜的《田舍》做注: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
老杜生性嶙峋,五蕴多刺,笔下的枇杷却有荒僻幽闲之味。原来老杜之味,也有田舍的荒僻味。
荒僻是我的院子,很小。除了枇杷、石榴,多栽了三五棵,想来亦无妨。
多叫了三无声,是鸟儿额外的馈赠。欣欣然,叫声和夏气都让人心里一动。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黄亚明,安徽岳西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诗歌、散文、专栏400余万字散见报刊。曾获孙犁散文奖、安庆市文艺奖、安徽省社科奖等十余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