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6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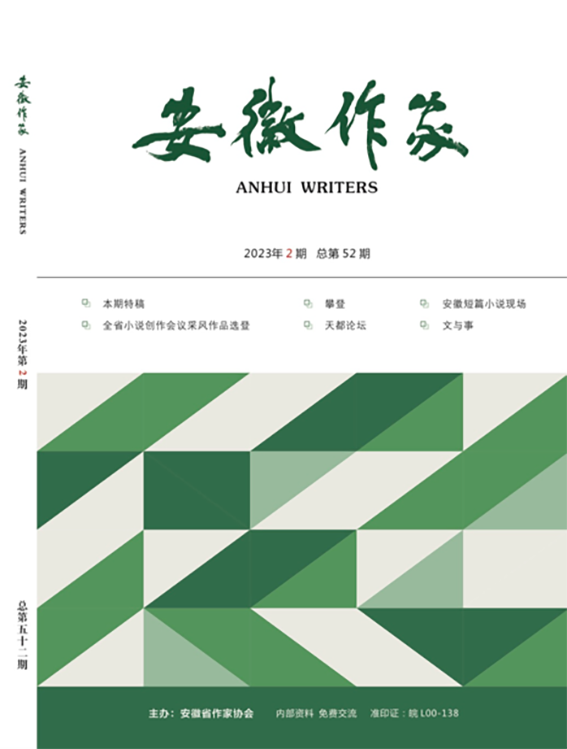
作品欣赏
温暖的花海
苗秀侠
渐近陵园时,小路两边厚密的花海扑面袭来,几乎将她与车完全淹没。按指示牌引导,她轻抚方向盘,略带点力,右转至一条新水泥路。新路从鲜黄的油菜花地里犁过,逶迤成一个问号形状,就像一句写在地上的祝福。
到了陵园大门口,她才发现,原来进出陵园,新增了这样一个环岛,进来的车辆,要从油菜花地里绕行一个半圆;出来的车辆,直行,缓解了祭祀高峰期的拥堵。
泊好车,在停车场站一会儿,调整一下情绪。四年没来了,一切仍是熟门熟路的样子。陵园大门东旁的一溜店面,门口摆满菊花,有盆花,也有抱花,黄菊白菊粉菊紫菊,粲然怒放,宛若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她喜欢盆花,花泥能让花儿绽放得长久一些。中盆三十元大盆五十元,她挑了两只中盆,插着黄白雏三样菊花,小小的紫色雏菊,有几分俏皮,小仙女一定喜欢。
买了花,是否再买黄表纸,她有些踌躇。问店家公共祭烧区还在吗?四年前她来烧纸时,就是在园内桥南西侧的公共祭烧区完成的。很有特点的地方,墙上雕刻着属相图案,图案下是一只只水泥砌的池子,根据逝者属相,在池内焚纸。店家摇摇头说,早扒掉了。看到她脸上的无奈样,店家又说,只要能把纸带进去,可以在墓前烧。可以吗?连问了两句,得到店家肯定后,她决定买两捆黄表纸,好几年没来了,两捆纸不算多。店家从床底下掏出沾着草屑的纸,拎了拎,有些重。店家说:“你自己带不动,我帮你吧,你先进去,过会儿我送给你。”
她说了墓园区号,就拎着盆花进去了。
穿过高高的园区门楼,很快走过弓形小桥,进到墓园内。一片耀眼的鲜花世界,扑面而来。这荒郊野外的墓园,因有这些绽放的鲜花而显出生机。这个被世间人铺排出来的繁华,仿佛一个诗意的起点,通向每个人设定和以为的神圣的地方。
沿着松柏甬道,走近那个恒久之地。四年未见的小碑,因有周边鲜花的簇拥,并不显得荒凉。她用纸巾擦拭着墓穴的碑座和石碑,此时,一阵吱吜吱吜声传来,店家的脚踏三轮车到了。瘦削的三轮车厢,盖着一层看不出原色的旧布,店家跳下车,掀开布,拎出来两捆黄表纸,又递了一盒火柴给她。她连忙道谢,居然,她都忘记火柴的事了,看来店家经验老到得很。店家又把另外半捆纸,送给了甬道东侧墓园的一对中年男女,那对夫妻正在给一座双位墓穴上香。
解开捆纸的塑料绳,两捆没有约束的黄表纸,噗地摊了一地。一边花纸,一边和小仙女说道起四年未来的因由。花纸的技术至今没有学会,她把纸对折起来,装模作样用指头搓捻了半天,纸还是原先桀骜的样子。她只好把纸握成帐篷形状,在碑前放好,点燃起来。火苗夹着青烟,在风里舞。“小仙女,你知道的,大前年,做了一个小手术,就耽误了时间,没来看你了;然后,人间的疫情,三个清明节都没能来,这次,妈妈终于成行了。今天的太阳真好,到处都是花儿,蚕豆花原来不光有白色的,还有淡紫色的呀;豌豆花开得真热闹,妈妈在路上都看到了。小时候妈妈喜欢掐豌豆花戴在耳朵上,当作耳坠,还唱着儿歌。想听吗?豌豆花儿朵朵,开在地心窝窝;爸爸摇耧耩地,妈妈撒肥春播。是不是很土啊,小时候唱着可好听了。那片芦苇呢,开着的花居然还是去年冬天的白絮花,从冬天走到春天,芦苇戴着的那顶厚棉帽,你说热不热啊。”
她嘴里絮叨着。从未像今天这样放松地絮叨,或许,疫情放开了的原因,更主要的,她退休了,出来不用再请假了。
她的腔调是开心的,就像来看一个老朋友,和老朋友叙家常一样。最开始来祭祀时,未进墓园就泪流满面,到墓碑前已经泣不成声。那时候,她一年要来三次,一次清明,一次农历的十月十五,一次春节前的年三十。不知何时,她来的次数少了,先是减成一年二次,后来一年一次,都是在清明节前。二十年来,再忙,一年一次来看小仙女,是一直的坚持,直到有了疫情。疫情前的那个春天,她做了个小手术,没能成行。最后一次来还是2018年的清明节。往返来去中,年岁一点点堆积,就跨过了五十岁的门槛,流泪的次数少了,更多的是和小仙女说说话。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在小仙女面前说,说对了说错了都不打紧。
小仙女九岁时,那场做梦都没想到的疾病来袭,小仙女走了。病痛里的最痛,她全部品尝。没想到的是,尚未擦干眼泪,伤痛还没愈合,新的伤害再次来袭。前夫痛心疾首地说,女儿在的时候,他是坚决不会离开家庭的,因为他爱女儿,现在女儿不在了,他重新考虑后,决定告诉她,他们还是分开吧。他早就不爱她了,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已经三年了。真的,三年了。他说这些时,口气是委屈和无辜的。其时,夜晚黑灯瞎火,两人并头躺在枕上,被窝显出空旷。她听到这些,居然是安静的。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动不动,身体渐渐变得冰冷,是一种死亡才有的冰冷。
她第一次体会到活着是可以成死亡状的。
他早就随着新的爱人到远方生活,而她,也离开了那座小城,调到省城工作。独留下女儿在苍茫的墓园。当初买墓地时,刚刚开发的陵园,一片荒芜,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空墓穴群里,女儿的单穴小碑显得那么卑微。这也是她每每来祭祀时哭泣不止的原因。后来,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了,陵园里的墓碑就竖满了,女儿所处的这个世界,变得热闹起来。
“小仙女,你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你是笑着看我们啊。记得你喜欢穿白袜子,很长的白棉袜,可以盖住膝盖,那套粉色连衣裙,也是你最喜欢的。你就是穿着粉色连衣裙和白棉袜,参加六一儿童节表演的,那段集体表演的舞蹈非常非常棒,其中你最棒。从三岁起你就在市少年宫学舞蹈了,你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舞蹈演员……你还喜欢弹钢琴,那时候房子小,打算暑假过后分到新房就买钢琴,那时候学校新建了职工宿舍大楼,你爸爸是有些名气的老师,完全能分到福利房的……小仙女啊,我说得太多啦,你烦不烦啊。不要烦啊,我能跟谁说呢?”
欢腾的纸灰像蝶儿飞舞,旋起一阵阵滚烫的热浪,舔着她的脸和头发。
“哎,你怎么能烧纸呢?你瞧,你还要烧这么多!不能烧!”
一个男声从身后传来,切断了她和小仙女的对话。她有些愣怔地转过身,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笔直地站着,穿一身青灰色保安服,满目严厉,狠狠盯着飞旋的纸火。她想赶紧起身作个解释,才发现,她的脚蹲麻木了,制约了起立的动作。
“瞧瞧你,居然,买那么多纸。疫情放开了,烧纸没有放开啊。你不知道吗?真是的。你以为能躲得过去啊,烧纸不冒烟啊。”他愤愤地说着,仿佛为自己的失职懊恼,声音越发大起来。
她蹲着仰视着他,有太多的抱歉。她不知道,她怎么就在墓碑前烧纸了。这些年祭祀时禁止烧纸,她明明是知道的,然而,店家一说只要能带进来就能烧,她一秒钟没犹豫就决定买黄表纸了。四年的相隔,她已经顾不得许多,她太迫切进到墓园里,让纸变成火,让火成为蝶儿,在蝶儿的飞舞里,她跟女儿说说话。那么多要说的话,没有纸蝶的飞舞,怎么说得出来呢?
终于站起了身,有些趔趄。她本想说些什么,发现说什么都有狡辩的嫌疑。她万般羞愧地小声说:“以为可以烧呢,这也不是山林,周围都是庄稼地……”
“无论啥地方,早就规定都不能烧纸啊。禁烧你不知道吗?你说,我是罚你款呢,还是不罚你款呢?”男人走动了几步,扫视着地上摊成一溜的黄表纸。她以为男人会一脚踩过来,把火灭掉,把纸踢飞。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她犯规了,要被制止,就得这样,这也是男人的职责。但男人话锋一转:“你买多少刀纸?”
“买了两捆。多少刀没问。”虽然担心会按购买纸的多少罚款,她仍然诚实地回答。
“那就是四十刀。你瞧你买这么多有啥用?买两三刀意思意思不就行了。”男人的声音更大了,一边说着,一边弯下腰,把地上摊的纸全部收拢起来,抱在怀里:“这纸,按规定要全部没收了。”满满的一大怀,像抱着一怀的黄菊花。地上正在燃烧的纸,不知趣地旋成几朵灰蝶,跃跃欲飞。正如男人说的,地上的纸,也就两三刀的样子,最多不超过五刀,因为,刚点着没多久,而且,没有花好的纸,不蓬松,烧起来慢很多。男人抱着纸站着,并没有立即走开,反而指着地上着火的纸:“你纸不花就烧,有啥用。”
“我不会花纸,试了,捻不开,还是原样子……”她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所措之境地,忐忑而羞愧。
突然,男子蹲下身,把怀里的黄表纸全部放到地上,两手搓了搓,抓过一刀纸,恨铁不成钢地说:“纸要这样花,对折起来,十个指头要一起动,大拇指最关键,朝上推,下面的指头朝下扒拉……”
他飞快地花开三刀纸,花得真漂亮,扇形,层层叠叠,像盛开的菊花瓣。她也连忙抓过一刀纸,跟着学,然而,她仍然没能花开,那刀纸在她的手指间仿佛凝聚的时光,动也不动。
“其实光这样花开了也不顶用,得先把一张一百元的真钱铺在上面,挨着铺,铺一次,用手拍打一次,钱才能印上去;要一张一张地铺,一张一张地拍打,铺完了,拍打完了,再花纸,烧了才管用……”男人边说,边示范着铺钱和拍钱印钱的动作。他张开粗糙的大手,像个魔术师那样,先做出铺钱的动作,然后,拍打着黄表纸上根本没有的“钱”。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铺钱,再拍打。她想到旁边的包里应当有百元大钞,决定去拿过来,让他铺钱印钱。她这个念头刚起,男人猛地站起身,声音又加大了几分:“你说,我是罚你款呢,还是不罚你款呢。你烧这么多纸干啥,你真是的,真是的。”絮叨着,猛地弯腰抱起地上的黄表纸,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开了。
男人只抱走了十来刀纸,余下的,都还原封不动地摊在那里。
她盯着男人远走的背影,一脸的泪就没来由地泼出来。她闭上眼睛,任由泪水奔涌。明艳的阳光,搂头盖脑罩住她。“小仙女!”她喊了一声,忍不住哭出声来。
已是中午时分,来祭奠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安静的墓园,只有她一个人。她一下放松了,再次蹲下身,学着男人的样子,摊开一刀纸,铺“钱”,印“钱”。她努力拍打着黄表纸,那一缕一缕的阳光,也随着她的掌声,被拍进纸里。之后,她双手托住纸,十指有力地捻动,纸们听话地排队布阵,成为松软的层次分明的扇形菊花。
花纸,成功了!
抓起花好的一刀纸,丢进火里,嘭的一声,重新燃起的纸火,再一次烫灼着她的头和脸。旋转着燃烧的黄表纸,渐成灰蝶,在愉快地飞舞。在灰蝶的舞蹈里,她又跟小仙女说道起了被中断的那些话。
两只小小的菊花花篮,在碑座上放好,那几簇懵懂的紫色雏菊,睁着无辜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她。伸出手,她轻轻抚摸着刻在碑上的字,就像弹拨一只旧琵琶。碑的颜色旧了,字的凹槽也浅了,曾经苍天可鉴明月可明的两人,早已天各一方,唯留下这并排着的两个名字,验证着海枯石烂的谎言。
然而,终究是爱过的,那些明亮的青春和远大的理想,那朝朝暮暮的追随,那十指交握苦乐与共的相守相依,都不曾在年月里缺席,如此,就算被定格在石碑上,也不枉此生了。
轻叹一声,她有了个决定。明年清明节前,她要找陵园管理处的人,给碑出个新,给碑上的字再描一描。她要让过往的岁月,显出该有的颜色和样子。
天空响起明亮的鸟鸣,一阵云雀快速掠过,飞向远方。墓园外围的农田,青麦穗举着细碎的花朵,油菜花织出铺天盖地的炫目金黄。那无边的花海,密密实实地包围着她,散发出一股股穿透岁月的温暖醇香。
(选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苗秀侠,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艺术界》副主编(主持工作)。在《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随笔》《作品》《长江文艺》《芳草》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有小说和散文入选年度作品精选集、《中国文学年鉴》等。出版《遍地庄稼》《迷惘的庄稼》《农民的眼睛》《皖北大地》《大浍水》等作品。曾获老舍散文奖,安徽省政府社科奖,北京文学奖,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