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4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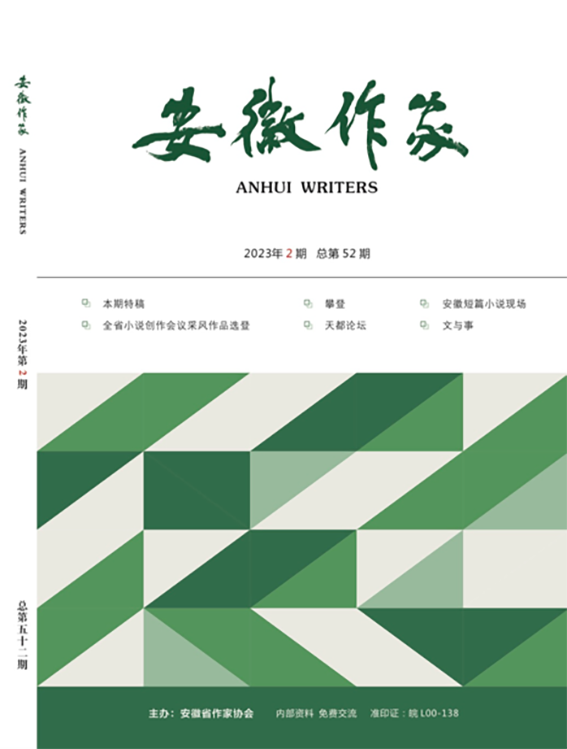
作品欣赏
小情歌
张诗群
一
老人姓马。阿蛋笑嘻嘻地鞠一躬,马爷爷好。身子一弯,背上的琴盒翘起来,“咚”的一声磕到了玻璃橱窗上。马爷爷面色宁静,此时露出一丝儿笑意,说,你从桃村来的?阿蛋说:不是,我在艺佳教吉他,小高书记打电话说了您的事,我就来了。
马爷爷看着阿蛋,嘴角的笑意略深了一些,脑袋轻轻摇晃着,类似于某种轻微的老年疾病。
马爷爷大名马复生,是本县荻蒲镇人,早年投笔从戎,一生南征北战,离休前是省城一家军事科研机构的军转干部。这次专程从省城来,是去桃村找一座坟。这是小高书记在电话里说的。
找坟?阿蛋差点把眼珠子瞪了出来。大学毕业这几年,因为经常参加公益演出,阿蛋成了团县委的青年志愿者。他唯小高书记马首是瞻,有时教教留守儿童弹吉他、有时跟一队人马轰轰隆隆开进村里搞义务宣传,有几次还帮人找过走失的猫猫狗狗,阿蛋不嫌烦,乐呵呵的,反正年轻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但这回,居然让他找坟?
说开了,才知道也不是小高书记揽的事。一年前,马复生打电话到县委,要找一个叫田阿妹的老坟,田阿妹是大湾镇桃村人,解放前去世的,去世时才十几岁。民政部门查来查去,最后答复查无此人。马复生的电话于是隔几天打一次,说县里解决不了他就要去找省委,民政部门实在没辄,想起团县委最活跃的志愿者阿蛋是桃村人,于是几经转手,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阿蛋。但是关于田阿妹的更多信息,无从得知,成了一个谜。
阿蛋瞟了一眼手机,刚好九点半。阳光很暖,白色二手奇瑞车沐浴在阳光里,白得有些晃眼。阿蛋打开车门,扶马复生上车。马复生伸手轻轻挡了一下,表示自己不需如此照顾。的确,除了轻微摇晃的脑袋,以及土坷垃一样从两鬓散落到下巴的老年斑,马复生一头银发,腰背挺直,步态沉稳,仍保留着军人风度,一点也不像小高书记说的耄耋老人。
白色奇瑞向桃村一路奔去。正是深秋,出了城,甩过城郊的几幢楼房,两边的景色绚烂开来。公路蜿蜒,像一条柔软的缎带,飘荡在田畴山野间。大湾镇地处县城最西部,因地势偏僻,山道难行,这些年发展缓慢,正因如此,倒保全了自然风貌的原生态,被誉为林县最后一片净土。
马复生看着窗外,忽然自言自语道:山还是那山,物是、却人非啊!声音苍苍的,透着暮气。
阿蛋扭过头,向窗外看了一眼。此时,深秋的诸子岭依然叠翠连波,山脚下白墙黑瓦,散落着十来户民居。一层雾岚,袅袅如烟。
窗玻璃下拉了一寸,钻进来的风吹乱了马复生的白发,仿佛一篷风中的白苇。马复生的喃喃自语勾起了阿蛋的兴趣,阿蛋说,马爷爷在这里打过仗?
马复生叹了口气说,我在这里读过两年中学,然后参了军,就出去了。
阿蛋问,是培锋中学吧?
马复生惊喜地说,你知道培锋中学?
阿蛋说,当然啦,我林县人嘛。
诸子岭是林县的红色地标。抗战时期,诸子岭上驻扎过新四军的一支队伍,打过几次大胜仗,抗战快结束时,中共林县县委在山脚下办了个早期的临时初中,就是培锋中学,但只办过两年半,就因战事紧张停课了。这些史料如今被刻成路碑、谱成歌曲,林县人几乎无人不知,阿蛋自然也熟悉。
马复生话不多,阿蛋注意到,只要一说话,马复生脑袋摇晃的频率就快一些,像安了个不受控制的小弹簧。沉默了半晌,马复生又问:小伙子,田阿妹的名字,你听说过没有?声音发颤,小心翼翼的。
阿蛋正要说话,连接车载音响的手机铃声忽然唱了起来: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
阿蛋接通了电话,不耐烦地喊,小玲子,说!你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一个女孩的声音像灌了蜜,阿~蛋!你到底考不考嘛?你一考准能过的哟,么么哒!
考什么呀考!小玲子你是知道的,我要当歌手!我要去上海参加海选!阿蛋回答得振振有词。
死阿蛋,你个臭蛋!坏蛋!笨蛋!告诉你,你就等着和我吹了吧你!女孩的声音从温柔秒变强悍,“喀嗒”一声,气呼呼地挂了电话。
阿蛋转过脸,对马复生不好意思地呵呵了两声,说,小玲子,我女朋友,她妈说,我不考个编制的话,就别想和她好,她就一天到晚逼着我考这考那的,烦死了!
马复生靠在椅背上,没有接话。过了一会,马复生忽然又问,小伙子,你姓什么?
我姓林,林阿坦。阿蛋说。
二
桃村离诸子岭十里地,在山路上拐几个大弯就到了。车子停在一棵粗壮的枫杨树下,树旁一条清悠悠的水渠向前流淌,渠边的满天星、水竹和山桃草早已过了花期,却也绿意未凋。枫杨树下聚了几个老头,站着两个,坐着两个,围着一张石桌对阵下棋,一树浓荫撑出一个椭圆形的场院,场院边上,立着一栋两层的小楼。
车一停,下棋的俩老头抬头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对拄着拐站着的秃顶老头说,你二犟子孙子回来了!另一个老头问,谁?这一位说,阿蛋呗,还有谁。
阿蛋和马复生一前一后下了车,正要说话,水渠边突然窜上来几只胖乎乎的大白鹅,伸长脖颈,抖开翅膀,“嘎嘎”叫着向马复生冲过来。秃顶老头喝了声“作死啊”,举起拐杖把鹅一只只又赶到了水里。
马复生左边转转,右边看看,问阿蛋,这是哪?
阿蛋说,桃村啊。指指二层小楼,这是我家,又介绍拄着拐的秃顶老头,这是我爹爹。在桃村,爹爹指的就是爷爷。
乍一听到田阿妹的名字,几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不约而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马复生拱拱手说,几位老哥好好想想,四七年,她十六岁,就没了,那一年闹伤寒,培锋中学死了不少学生,田阿妹就是那一年殁的。
几个老头愣了好半天,阿蛋的爹爹忽然说,你说的是田小妹吧?我记得田小妹就是四七年走的,书读得好好的,抬回家没几天就走了,说没就没了。
马复生踉跄着抓住阿蛋爹爹的手,老哥哥,她埋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阿蛋爹爹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就不知道了,我比她小几岁,那时候才这么高。阿蛋爹爹用手比了个“这么高”的高度,思绪和眼神都悠远起来,啊呀她长得可标致,头一年刚订了亲,两边都是大户人家,订婚席面摆了十几桌,把村里老少爷们都喊去吃酒,我小,家里穷总吃不饱,也跟我老子一块去了,吃了个肚子溜圆,到今天都还记得。
马复生静静地听着,脑袋不由自主地摇晃,嘴唇也轻轻抖动起来:老哥哥,桃村还有谁知道她埋在哪?
阿蛋爹爹嘴里牙疼似的嗞了半天,说,五保户漆老头子可能知道,可是他聋了呀!
阿蛋急了,说,爹爹,你再想想,再想想。
想起来了!小玲子大姑奶奶!田小妹和她关系最好!阿蛋爹爹激动起来,拐杖“笃笃笃”地敲击着地面,使秋天的桃村陷入了回忆。
三
小玲子在接到阿蛋电话四十分钟后,赶到了桃村。
一见面,小玲子就噘着嘴,狠狠地剜了阿蛋一眼。阿蛋嬉皮笑脸地把小玲子拉到怀里,给了个大熊抱,算是道歉。小玲子气呼呼地挣脱出来,扭过脸却抿嘴乐了。马复生说,姑娘,辛苦你了。小玲子两只手在胸前一阵乱摆,脆生生应道,不辛苦不辛苦!小玲子娇小秀气,头发烫着卷,稍微一动,两只银色大耳环就叮儿叮儿地轻响,像自带着两只随风摇曳的小风铃。
天还不太冷,大姑奶奶已穿上了绛红棉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大姑奶奶快九十岁了,一笑起来,咧开没牙的嘴,像个婴孩。老虽老,大姑奶奶耳聪目明,听到“田小妹”三个字时,吃惊地盯着马复生,瘪着嘴说:喜喽!早喜喽!小玲子在一旁翻译说,死了,早死了。
马复生一着急,就有些气喘,他喘着问了好几遍田小妹埋在哪,大姑奶奶却自顾咿咿呀呀地说开了,一边说,一边用袄袖擦眼睛。马复生看着小玲子干着急。小玲子翻译说,田小妹死的那一年,她订了亲的婆家雇了个大花轿,吹吹打打地来到村上,把她的牌位迎回去了。还没拜堂的对象也来了,差点哭晕了过去。
马复生咳了一声,嗓子就哑了。他哑着嗓子问,那她……埋在哪?
付强生态园坐落在村东。沿一条村村通公路走进去,远远就看见一个带长廊的木制门楼,门楼上挂着四只红彤彤的灯笼,映着四面山色,格外艳丽醒目。长廊外,是一口占地两亩见方的池塘,旁边立着一块木牌,上书“垂钓处”三个赭黄色楷体字。池塘四周,是各种树木苗圃,桃树林、梨树林、油桐树林等各自成片,矮小一些的桂花、石楠和栾树苗圈着竹篱,随处可见的耳草和毛蕨贴地而生,触目所及是植物的海洋。
真的就是一片海洋!绿色的汪洋大海。乌泱泱一片,已经被开垦成平坦的林地,被成千上万棵树木占领,被波浪般汹涌的绿色填平,连一个突起的土丘都看不见,更何谈墓与碑了。
马复生一站到这片土地上,就明显地激动起来,眼睛也不够使了,一会手搭凉棚远望,一会又钻进树丛里用拐杖划拉草皮,看看这边,又换个地方看看那边,越看越不对劲,焦急地问,大姑奶奶说的是这个地方?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阿蛋解释说,几年前,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这个叫付强的人,把这片山地翻了一遍,建成了生态园,每年水果成熟季都要举办采摘节,据说效益还不错,但是翻地的时候也没听说要迁坟啥的。
小玲子像做错了事,怯怯地接腔说,我不记得这里有过坟哎,小时候就没有,可能……早就没有了吧。
三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林地静悄悄的,阳光在树叶间柔软地穿过,光斑和树影交替闪烁,明明暗暗的,一片片浓荫,又一片片光明。
马复生突然恸哭起来。他耸着肩,张着嘴,老泪纵横。他泪眼模糊地望着前方的林海,老迈的嗓音撕心裂肺地呼喊着:阿妹啊!阿妹啊——
阿蛋的心里忽然像被刀子割了一般地疼。
四
吃过午饭,阿蛋执意开车送马复生回省城。小玲子在一家公司做财务,这几天不忙,也乐得伴驾同行。
奇瑞车穿梭在来时的公路上。车过诸子岭,马复生让阿蛋停了车,说要下车看看。
雾岚早已散去,午后的诸子岭罩上了一层秋阳的薄光,山色更加清晰明朗起来,露出了季节的真面容。一些深黄橘红揉杂在苍绿墨绿之间,仿佛印染的彩色缎面。山脚下,窝成一排的白墙黑瓦处,隐约可见美丽乡村建设的崭新气象,一幅水彩墙体画虽然看不真切,但旁边竖排的五个草体字却异常醒目:红色诸子岭。
马复生指着那一排民居说,那里,培锋中学当年就是在那里。
小玲子以手遮额,挡住晃眼的阳光,看了片刻说,田阿妹就在这里读书的,是不是?
马复生说,还有我,我和田阿妹,都在这里读过书。我早她两年,我参军走的那一年,她刚入学。后来,就闹了伤寒嘛,唉!
阿蛋问了一句一直想问的话:马爷爷,田阿妹是你的……女朋友?斟酌了半天,还是用了“女朋友”这个称谓。
马复生抿紧嘴唇,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加重语气说,未婚妻!准确地讲是未婚妻。大姑奶奶说的那个差点哭晕了的对象,就是我!
奇瑞车重新启动起来,回程的路上,在两个年轻人的好奇询问下,马复生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我和她,只有四天,四个星期天。马复生说。
马家和田家都是林县大户,两家并不熟识,马家在荻蒲镇,田家在大湾镇。马复生的姐夫是田家的私塾先生,觉得女学生田阿妹和内弟马复生脾性相近,两家又门当户对,于是做了牵线媒人。换了庚帖,办了订婚酒,亲事就算正式定了下来。因为订婚时年龄尚小,当时又有婚前不宜见面的习俗,也不知是哪一方先起的念头,两个未曾见面的年轻人尝试用书信来了解和认识对方。谁知,书信一通,惊醒了沉睡的爱神,信越写越多,话语也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缠绵。终于在这一年暑假,在培锋中学补课的马复生约田阿妹在诸子岭见面。
一连四个星期天,田阿妹天不亮就从桃村出发,踩着露水,走十里山路到诸子岭,与等在那里的马复生会合。见了面,两个少年又害羞又喜悦,心怦怦跳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傻话,傻话说说又停停,田阿妹就红着脸小声地唱歌,唱《望郎》,唱《我看槐花开未开》……
好听吗?马爷爷唱几句呗。小玲子打断了马复生的回忆。
马复生顿了一下,像是刚从梦里惊醒过来。他清了清嗓子,迟迟疑疑地唱了起来:
正月望郎梅花开,大雪飘飘落下来,姐在房中烘炭火,开门扫雪望郎来。二月望郎杏花开,燕子双双飞进来,燕子衔泥多劳力,细语呢喃望郎来。三月望郎桃花开,姐靠桃树手托腮,千朵桃花朝下落,摘对仙桃望郎来……
这是《望郎》,后面不记得了。马复生说。
真好听哎,阿蛋你说是不是?小玲子问阿蛋。阿蛋也连说好听。
确实好听。马复生的嗓音尽管混浊苍老,像生了锈的哑锣,但那旋律婉转,像小云朵在天上飘着。
姐梳油头到门外,手扶槐树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看槐花开未开……马复生又唱起了另外一首。
太好听了。小玲子赞叹道。她捏起拳头去捶阿蛋的胳膊,阿蛋,你要是把这首歌改成吉他民谣,比你翻唱《小情歌》还要好,海选时一唱,保准炸裂!
是谁说我去参加海选就和我吹了的?啊?谁说的?阿蛋慢条斯理,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你还好意思说呢,小玲子回过头对马复生说,马爷爷您评个理,他前年就答应我妈要考编制的,可就是拖着不考,我妈对他就这么个要求。去年到长沙,今年又要去上海,海选是那么好选的?家里没钱运作,又没人给你编故事煽情,我们就是草根阶层,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行吗?
阿蛋不满地咕哝道,我又没说不考,年轻的时候谁还没个梦想,再说了,小高书记把海选亲友团都组织好了。
小玲子说,生活要有诗意和远方,可起码要生活不是?咱俩的未来也得考虑吧。我都打听过了,三小、五小招音乐老师,文化馆和少年宫明年也要招人,这都是你的菜啊阿蛋。
阿蛋没有说话。车轮轧到一块拱起的石条,很响地“咯咕”了一声。
马复生没有料到自己的回忆被两个年轻人的拌嘴突然打断,他一下子陷入短暂的空白,接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玲子回过神来,赶忙问,后来呢?
回忆又接上了。马复生说,后来,后来就这么见了几天。到了第四个星期天,我的课也快补完了,暑假一过,就要去参军,她也鼓励我报效祖国。这天分别时我们都很难过,又哭又笑的,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太阳落山时我俩一口气跑到县城照相馆,肩并肩合了张影。这张照片我一直带着,可惜呀,最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丢失了。这是以后的事了。
暑假过后,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皖南支队。记得是快要入冬,比这个时候还冷一点,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我随部队在邻县驻守。一天下午,我父亲跌跌撞撞地跑来,告诉我田阿妹病逝的消息,简直是天崩地裂,我捶胸顿足地哭啊,我父亲也陪着掉眼泪,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哭成了泪人。谁能想到呢,我们在信里还说一放寒假她就来看我的。说到这里,马复生的眼里泛出泪光,完全陷入到悲伤的情绪中:我就和父亲商量,田阿妹生是马家人,死是马家魂。后来,我家就抬了顶轿子,去桃村迎回了她的牌位,我双手捧着,安放在我们马家的祠堂里……
上了高速,道路明显顺畅了起来,两个小时的车程已走了近一半。窗外天高地阔,只听得车轮刷刷的声音和马复生低沉缓慢的讲述。
马复生说,也怪,年轻的时候老想梦见她,越想梦见,越是梦不见;现在老了,她天天到我梦里,总是在唱那些歌,唱着唱着我就醒了。我就想啊,我和老伴有儿有女,她孤苦伶仃的,她是太孤单了,要我去看她,要我去找她……唉,阿妹啊,我是来了,你在哪呀?
五
马复生的家在瑶海路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原本是单位的家属大院,在马复生退休之前,军事科研机构就已迁址别处,小区居民搬的搬,迁的迁,也就慢慢萧寂了。两年前风传这片地段要新建一个国际连锁超市,仅剩的几户老弱病残等着拆迁,但一直没有等来。
院子里的水杉落了一地枯叶,没有人打扫,也少人踩踏,就那么新一层旧一层地铺着。红砖砌成的镂空围墙外,稀疏地栽着几篷剑麻,一条青石小路沿着围墙通向幽暗的巷道,巷道连通着另一片居民小区,再往后,就是喧闹的市声。
马复生的家在三楼。楼梯逼仄,拐角处堆放着废弃的煤球炉、简易鞋架等杂物,各家各户的门都关得严严的,二楼的门锁已有锈迹,显然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马复生摸出钥匙,抖索着插了两三次,才打开了门。小玲子皱了皱鼻子,一股隐约的老人味和霉腐味交杂的气息迎面而来。两室一厅的屋子陈设简单,靠墙摆着老式的木质沙发,一张四方桌占着客厅中间的位置,旁边是两把陈旧的木椅。这是一间用旧了的老房子,饼干筒、纸箱、塑料包装袋、拖鞋和暖手宝、电火桶等物件挤满了窗台和橱柜的空间,此时,岁月的痕迹和这屋子里的老人是如此相称。
阿蛋在一排相框前站住不动。小玲子帮马复生张罗着倒了两杯白开水,递给阿蛋一杯,也站在那里,看墙上的照片。
墙皮已经泛黄,但仍然将照片衬托得分外醒目。左边第一幅是一位身穿军装的年轻军人,尽管是黑白照,但军人浓眉方额,眼神冷峻,有一股逼人的磊落英气。小玲子由衷地赞道:马爷爷年轻时真是帅啊!
第二幅,是马复生和一群战士的合影。战士们盘腿坐在地上,都咧开嘴笑着,身后是堆得高高的麦草垛。第三幅彩色照片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马复生已经老了,和老伴坐在中间,腿上各坐着个四五岁的孩子,身后高高低低地站着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第四幅是马复生和老伴的合影,老伴圆圆的脸,眉眼温和,对生活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第五幅是马复生出席什么重要会议的大合照,密麻麻的人影排成了三四排,要不是马复生过来指点,很难找到他的面孔。最后一幅,也是最大的一幅,是一张在照相馆做了加彩技术的女孩照片。
不等阿蛋询问,马复生说,她,就是田阿妹。
阿蛋的心忽然紧缩了一下,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心疼的悸动在心底漾开。
那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孩。剪着学生头,脸微微地向上侧仰,眼睛并不很大,单眼皮,但纯净清澈。脸庞清瘦,嘴唇微启,似乎含着淡淡的笑意又似乎没有。那是一张不属于这个年代的脸,一张清新稚嫩的脸,仿佛早春原野上一根带露的小草,怯怯地迎着朝阳,有几分懵懂羞涩,让人心生怜爱。
马复生看着田阿妹的照片,像是在和田阿妹说话:那是她送给我的,原来只有一寸,小小的黑白照,我拿到照相馆放大了,加了彩挂墙上,一抬头就能看见。
小玲子往阿蛋身边靠了靠,挽住阿蛋的胳膊,仰起脸看一眼阿蛋,又看一眼,眼神异常温柔。阿蛋抽出胳膊,搂住小玲子的肩,此刻有些说不清的感动和柔情,在两个人心头流转。
就在这时,门忽然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拎着一只大保温筒走了进来。
马复生似乎惊了一下,他轻轻摇晃着脑袋,双手垂下来,有些不安地看着进门的女人。
你中午去哪了?打你电话打不通,又忘记开机了吧,害我跑一趟空。女人一进门就开始埋怨。
开了的,开了的,声音小,没听见。马复生喃喃道。
哟,这两位是——
我们是送马爷爷回家的。我叫阿蛋,这是我女朋友小玲子。阿蛋抢先答道。
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我爸岁数大了,麻烦你们,麻烦你们。
原来是马复生的女儿。
马复生也连声附和,是的是的,真是多谢他们。
忽然,马复生的女儿语气一转:又去找那个田阿妹的坟了吧?爸你这是干什么?找着了又能怎样?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让别人怎么想?
马复生嗓子眼里吭吭了两声,脸上有讪讪之色,看了阿蛋他们一眼,没有说话。
女人打开保温筒,把饭菜一样一样取出来。有青菜萝卜、几片排骨、木耳烧豆腐,还有几只红虾。又想起什么,女人抬起头问阿蛋,你们,也在这吃吧,我们去外面吃?
阿蛋看一眼墙上的钟,五点多了。连忙摆手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回去。立刻牵着小玲子的手,向马复生道别。
马复生的女儿也一起出了门,一路上,絮絮叨叨地叹起苦来。
也不知怎么想的,我爸真是老糊涂了,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活了一把年纪,不是不懂情啊爱的,但你们说,对我妈公平吗?我妈年轻的时候没有随军,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两个,容易吗?好不容易随军了,里里外外操持一个家,我爸就是甩手掌柜,工作又忙,根本顾不到家里。我妈走了十几年了,我爸倒好,想起他这个初恋了,从省里到县里到处打电话找她的坟。前年楼下的老刘还没搬走,他整天和人家老刘讲这个田阿妹,现在老刘搬走了,他找不到人唠,就到处乱跑,今天幸亏是你们给送回来,要不然出了事找谁去?我服侍他苦点累点不怕,我是他女儿,应当的,可这事,我们做儿女的心里总不是滋味,替我妈不值,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怎么办……
出院门的时候,马复生的女儿再次向阿蛋道了谢,沿青石小路朝巷道走去了。院子里的落叶苍苍一片,安静无声。阿蛋牵着小玲子偶一回头,看见马复生正默默地站在楼下目送着他们,孤零零的,像顶着一捧白雪的枯树桩子。
奇瑞车渐渐地开进了夜色。旋开音响,是多亮略带沙哑的嗓音:
你知道 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受不了 看见你背影来到
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了
最后谁也都苍老
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六
日子又回到周而复始。阿蛋参加了几场送文化下乡演出,被小高书记领着去看望了几个留守儿童,又去县电视台录制了道德模范颁奖晚会,很快,这一年就过去了。
新年刚过,阿蛋收到了上海发来的通知,歌手海选定在六月。筹办方在海选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应准备事项,选曲、乐器、个人简历,有无驻唱经验以及成长故事等等,群里乌泱乌泱的,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爱好者在这里聚集,聊天的,骂战的,推介自己的,发广告链接的,发演唱视频的,每天都闹哄哄的,像一个大集市。
小玲子隔三差五地还是会嘟着嘴,撒着娇,催促阿蛋准备编制考试,有时着急起来,眼圈一红,眼泪都快流出来。小玲子和阿蛋一个村子长大,可谓青梅竹马,但真正好上是在高二的时候。高考后小玲子上了财会类大专,阿蛋上了个艺术类二本。找工作却是倒了个个儿,大专生小玲子顺利地在本地一家上市企业找到工作,本科生的阿蛋却至今漂着。
艺佳培训机构的寒假班又忙碌了起来。阿蛋在寒假班教吉他,虽是临时性质,却教得认真。关于马复生的印象慢慢淡了,只在摸起吉他时他会想起马复生唱的那些小曲儿,于是自己编了谱,试着弹唱了几次,清新如山风吹拂,却没有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他们喜爱的是《灰姑娘》和《十年》。
清明节的前两天,阿蛋百无聊赖地泡在海选群里看搞怪视频。一个四川选手举着锅铲当麦克风,脸上抽筋似的在唱《成都》,阿蛋笑得嘎嘎的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按了接听,居然是马复生。马复生的声音苍老迟缓,听起来断断续续的。马复生问阿蛋明天能不能去省城接他一趟,他要把一块碑运到诸子岭来。
第二天天不亮,阿蛋和小玲子就一起上路了。赶到省城,还不到八点。马复生穿着一身军装迎候在门口,军装已泛旧褪色,有明显的折痕,是刚从厢底翻找出来的。左胸处,上下两排别着六枚勋章。阿蛋凛然起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几个月不见,马复生衰老了许多,面容枯寂,脑袋摇晃的频率和幅度也比上一次有所增加。他把阿蛋和小玲子让进屋,一块长方形的墓碑赫然映入眼帘。
碑是麻青色的,大理石的纹理细腻光滑。上方的居中位置,是一张彩色烤瓷小像,田阿妹侧仰着脸,清纯无瑕,嘴角似乎含着笑又似乎没有。下方写着“故妻马田阿妹之墓”,落款是马复生携儿孙的姓名。
马复生说,前些日子已托老家的亲戚看好了墓地,今天是正式修坟立碑的日子,老家那边请来帮忙的人都在诸子岭等着。
小玲子不解地问,可是,上次在桃村,不是没找到吗?
马复生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道,她说她孤单啊,天天在我梦里唱着歌,就那么看着我,我心里好大不忍……诸子岭好,我们在那里读过书,都记得那个地方……就是个念想了,就是个念想……
一路上天色阴沉沉的,车到诸子岭时,下起了毛毛雨。车一停,坡上走下来三四个壮年男人,从后备厢抬出墓碑,又向山坡上去了。马复生的一个侄孙走过来,扶着马复生慢慢地沿一条碎石小路也向山坡走去。
雨不大,雾濛濛的,山上的草树却渐渐都湿了。映山红开得炽烈,一簇一簇的湿红,十分耀眼,在雨雾中静默着。阿蛋搂着小玲子,站在一棵可以挡雨的大松树下,看着那些人忙碌。他们低着头,认真而细致,谁也没想去弄明白修一个空冢的意义,但他们知道,对将近九十岁的马复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墓碑栽进土里要拢坟堆的时候,马复生慢慢蹲下,抖索着从一只帆布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黑布袋,拉开抽绳,露出一缕枯草般的白发。所有人都愣住了,黑布映着白,那样醒目,像黑土地上的一捧白雪。马复生把白发轻轻理了理,又拉紧抽绳,颤巍巍地放 入土中,然后口中轻声地念着什么,周围的人肃立一旁,像在聆听着自然之声。
阿蛋牵着小玲子,默默地往回走。阿蛋忽然哼起了那首曲子:姐梳油头到门外,手扶槐树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看槐花开未开……
小玲子搂紧阿蛋的胳膊问,阿蛋,你还去上海吗?
(转自《安徽作家》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诗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文学作品刊于《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安徽文学》《边疆文学》《福建文学》《西湖》《雨花》《红豆》《岁月》等刊,出版著作多部,获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