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7-06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刘鹏艳佳作频发:小说《等候》发表于《青年作家》2023年第3期;小说《露薇在渝》发表于《海燕》2023年第3期,短篇小说《开始就是结局》发表于《飞天》2023年第6期;短篇小说《小燕子,穿花衣》发表于《小说林》2023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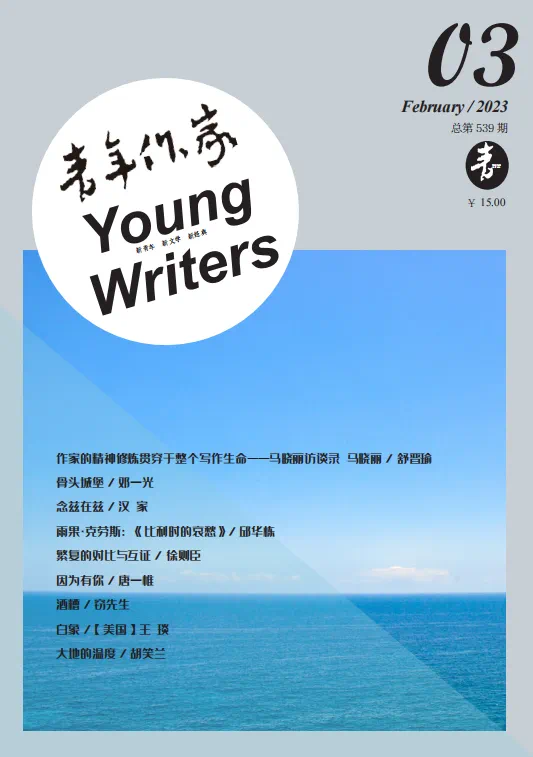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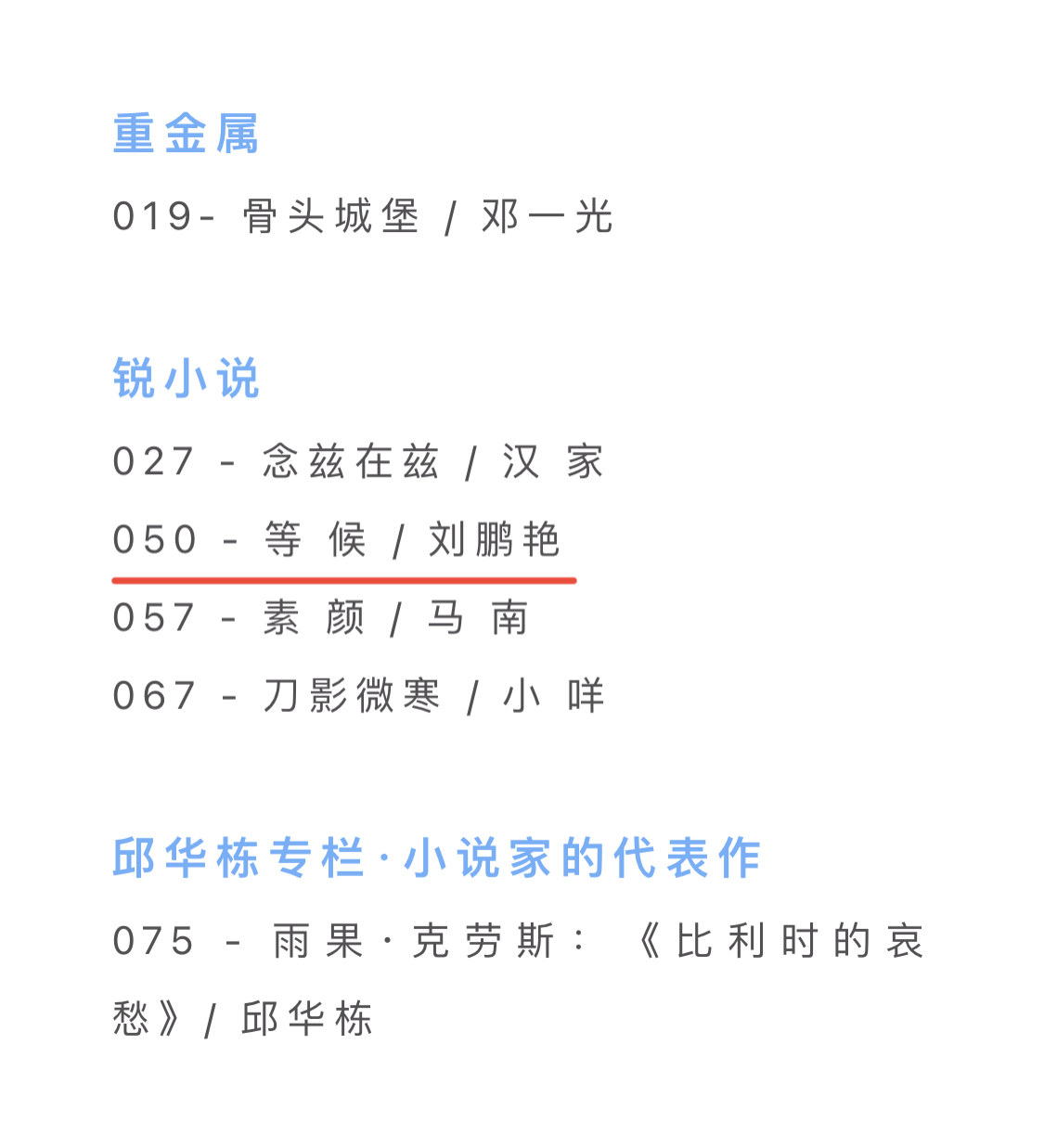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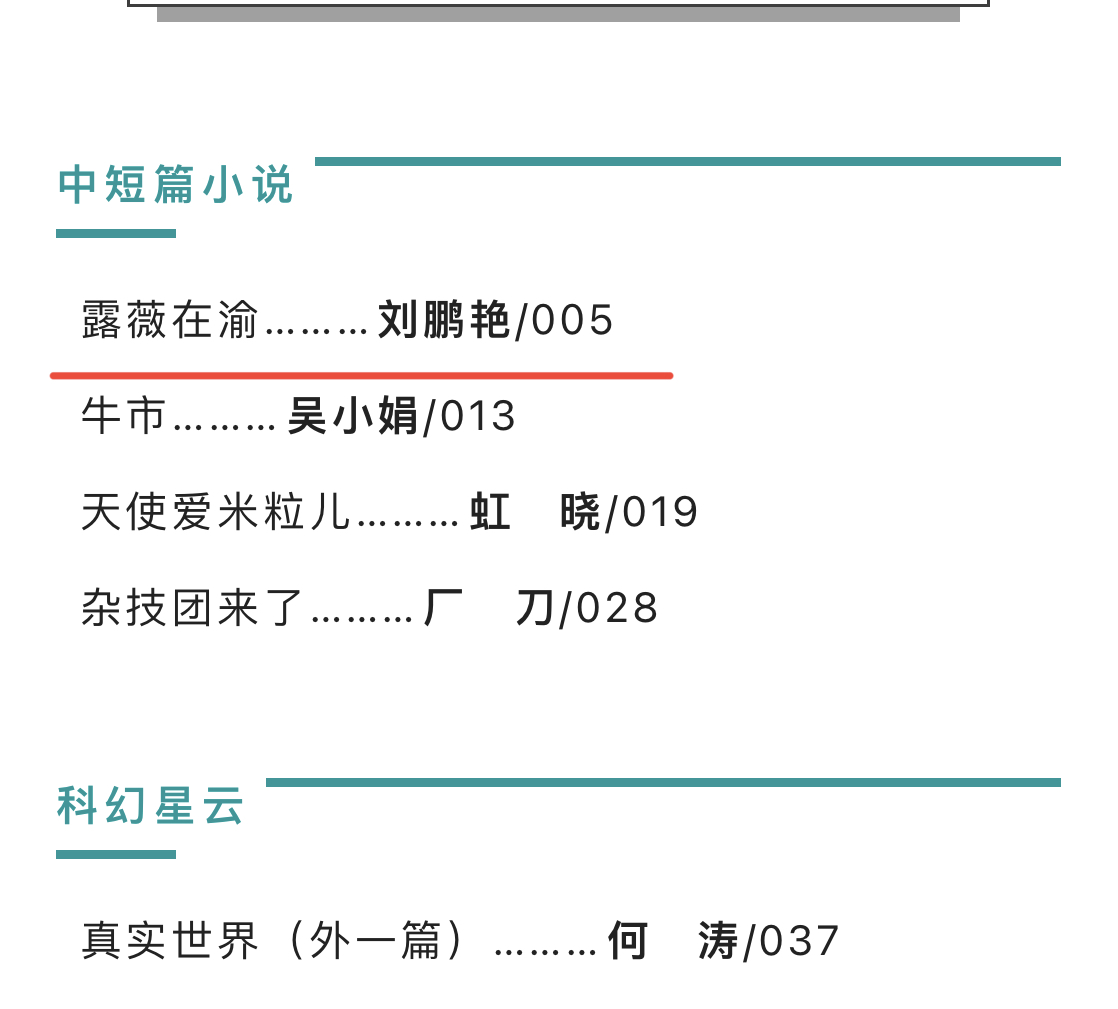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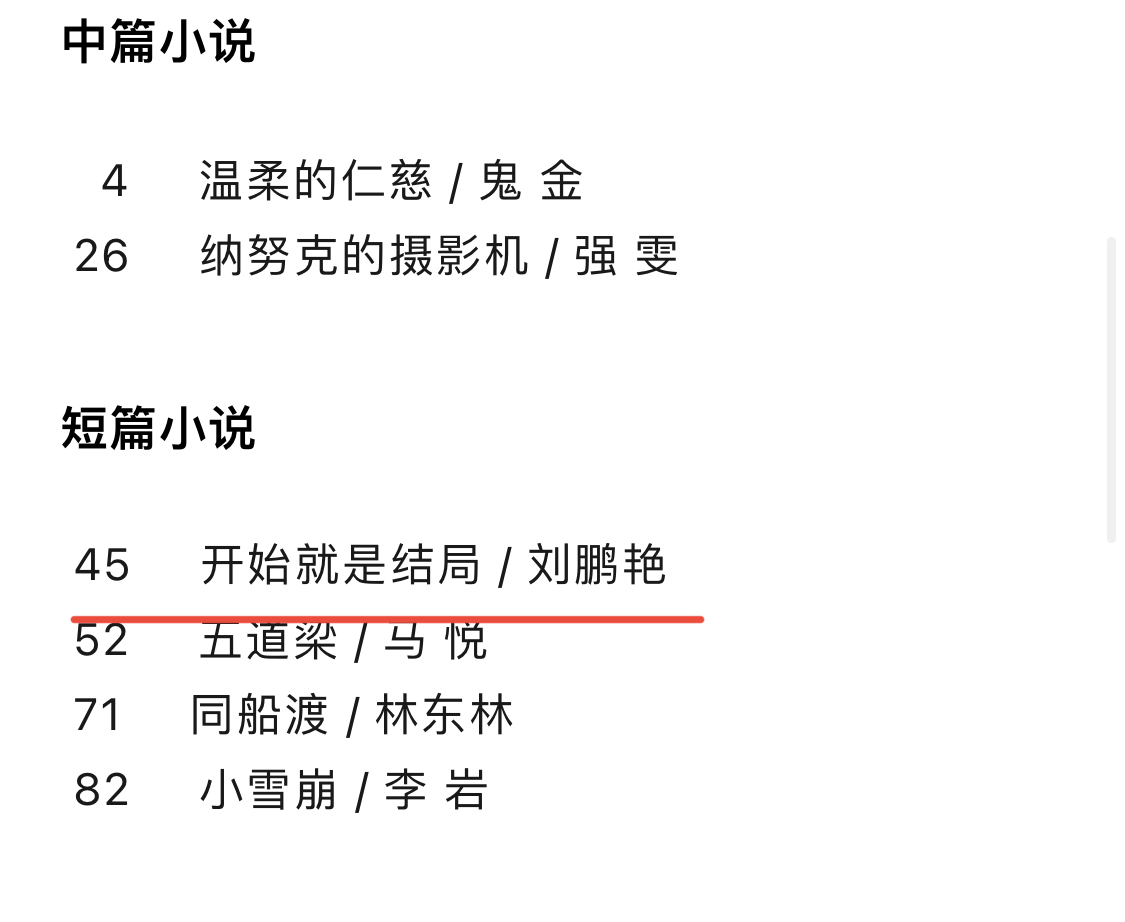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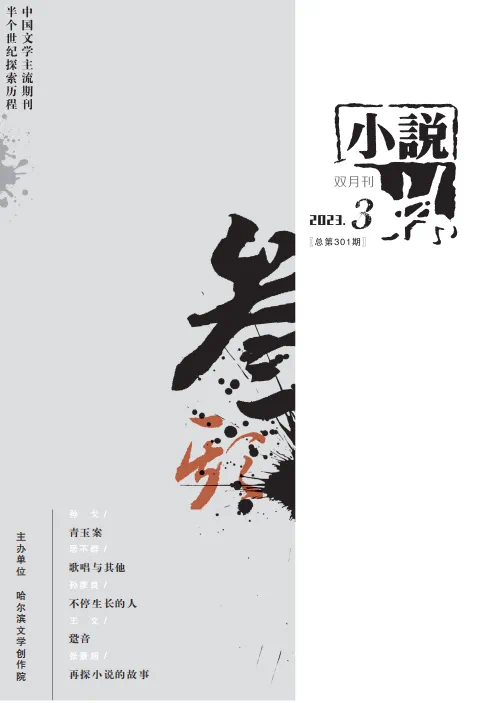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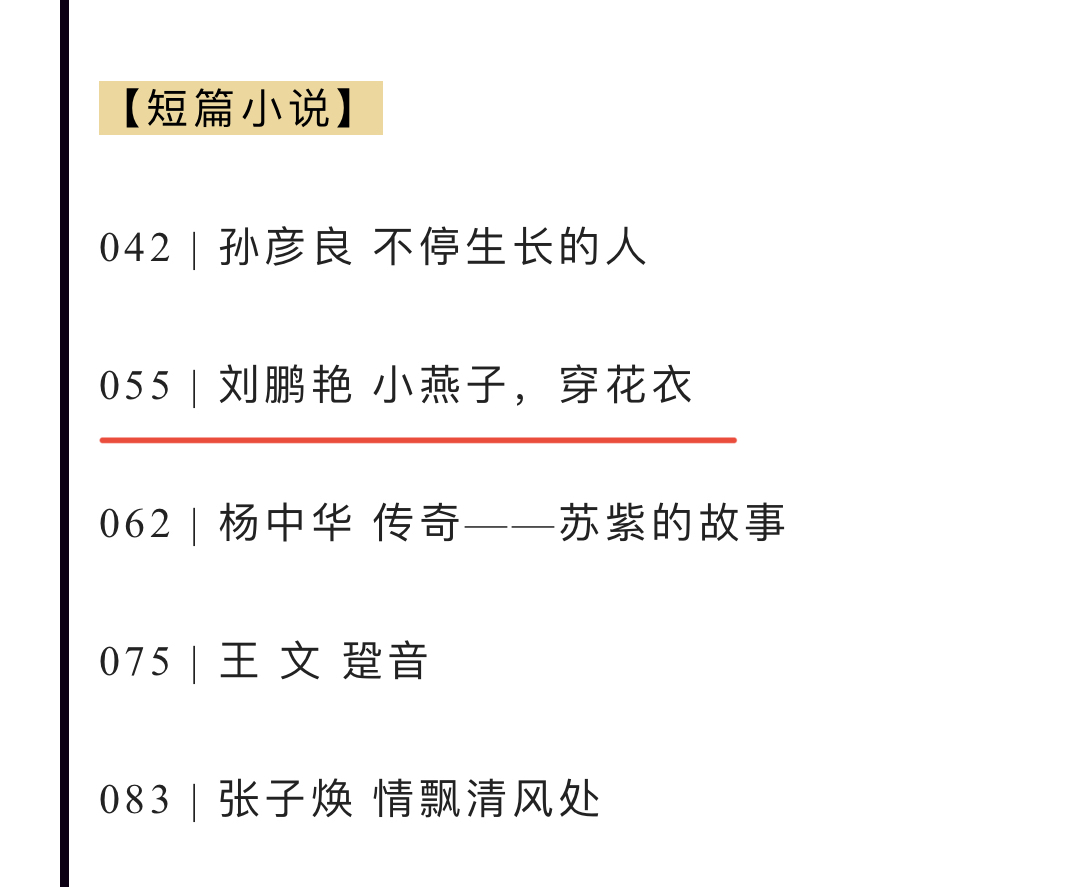
小燕子,穿花衣
刘鹏艳
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儿了。
那个春天,喃燕才刚满一岁,到初夏的时候,已经满院子乱跑,谁都拦不住。托儿所的老阿姨说,这丫头精怪得很,八九个月就会说话了,十个月就下地了,如今我是看不住她的。她妈若是来找我,我也这样说。老阿姨说这话的样子气鼓鼓的,好像那个十几个月大的婴儿给她造成了天大的麻烦似的。
事实上喃燕确实够给人添麻烦的,她的小嘴儿叭叭的,什么都会说,她跟她妈告状,说托儿所的老阿姨虐待她——“虐待”两个字当然是不会说,但她和她妈学样儿,小手比画着,墙,燕燕,站着。那意思是说,老阿姨嫌她爱哭,让她靠墙站着,靠墙还不是屁股靠墙,老阿姨让她对着墙站,玩具啊,图画书啊,小朋友啊,什么也看不见,没意思透了,真正的“面壁思过”。
燕燕,想妈妈,才哭。喃燕撇着小嘴儿跟妈说。
不能算是什么“过”,妈心疼得不得了,可也没辙儿,各家的情况都一样,厂里所有够不上幼儿园年龄的孩子,都集中在这家临时性质的托儿所,没断奶就送过去。产假总共就那么几个月,谁家也不敢为了心疼孩子,把活路给断了。说起来厂子算是仁义的了,给职工建了这么个托儿所,虽说雇的老阿姨都没什么文化,可孩子小,也用不上那玩意儿,平时吐了拉了哭了闹了,抱起来给哄哄就行,不然女同志当妈以后,多耽误社会主义建设。
妈工作的厂子是合城钢厂,数一数二的国营大单位,从乡下招工上来那会儿,差点儿没打破头。要不是五七办公室的表叔帮忙,还得在农村扎下去。扎下去就没有喃燕了,爸不可能娶个农村老婆。就是现在,合城的双职工,也不敢说日子就比别家强。只能说是一样平均的穷。端午或者中秋,才敢花钱吃上一顿红烧小仔鸡儿;遇上买手表、自行车或者电风扇这样的大件儿,得约着周边的工友凑份子“打会”,那几个月,就得节衣缩食。爸在地质队扛标尺,漫山遍野地跑,全省境内的每条河每座山爸都熟,唯独家里的锅碗瓢盆摸不着边儿。
所以妈想了想,还是笑着对托儿所的老阿姨说,您看在这么小的孩子的分儿上,她哭,就让她哭去,不碍着您什么事儿,就是别让孩子一个人憋在墙角,她怕。
老阿姨自知理亏,可也不能就这么折在一个十几个月大的黄毛丫头手里,于是噘着厚嘴唇说,我可不是不待见你们家孩子,你都看到了,我这儿的孩子可是论窝儿不论个儿,这边吐了,那边拉了,我是怎么都招人埋怨。我让她在墙角待着,那是为了安全考虑,你当妈的要这么说,我不管她就是,可着劲儿造去,到时候别又来怨我。
哎,哎。妈点头赔着笑。中午妈抽空儿过来,从食堂打了猪肝汤,拌在白米饭里,嚼烂了,喂给喃燕,真就像老燕子喂小燕子,一口一口的,从老的嘴里过到小的嘴里,一个春天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夏天,喃燕的腿脚可又健了些。托儿所里,比她小的也有,比她大的也有,男孩子更多一些,他们都是惹祸的家伙,老阿姨管不住,常常气急败坏地捉了他们打屁股,由得喃燕这样乖态的小姑娘自己管自己。喃燕已经交了朋友,两岁的梅燕。好巧不巧,梅燕的名字里也有个“燕”字,她妈和喃燕妈都在一个车间里,前后脚怀的孕。喃燕妈姓徐,梅燕妈姓凌,车间主任就喊她们一个小徐,一个小凌,俩人也都是好朋友。
托儿所里,不识字儿的老阿姨分不清楚,管梅燕叫大燕子,喃燕叫小燕子。梅燕妈来了,就叫大燕子妈;喃燕妈来了,就叫小燕子妈。两个燕子差不了半岁,差别可大,喃燕能说会道,不管是哭还是笑,动静都大得很,想不搭理她都不行;梅燕呢,虽说年长一些,话却说不大利索,人也安静,给她一个玩具,就静悄悄地一旁玩儿,多半天都不带吭一声儿。俗话说,三岁看大,这虽才一两岁,也能看出子丑寅卯了。喃燕是个不肯吃亏的,梅燕则憨得多。
在托儿所,喃燕和梅燕总是牵着手。有时喃燕闹脾气,一个人猫起来哭,梅燕去拉她,她也不理梅燕。总要等哭够了,喃燕才转过身,把梅燕的手牵上,两人又一起玩耍,跟没有伤过心一样,笑得嘎嘎的。要是有人抢梅燕的玩具,喃燕就把玩具抢过来,抢过来还不算,还要抡起玩具往人家头上敲,一边敲,一边说,打你,坏蛋。梅燕起先还瘪着小嘴儿,跟受气团媳妇儿似的,眼泪挂在睫毛上,将落未落,等喃燕把玩具抢回来,这才展颜呵呵地笑,拿手背一抹,什么事儿也没有。
那个夏天,厂里的蜀葵开疯了,到处是一人来高的蜀葵秆子,虽说是草本,抓地拔起来,倒比小树还高,红的,紫的,白的,粉的,黄的,单瓣的也有,重瓣的也有,叶大花繁,锦绣夺目地开成一片,箭茎条条直射,琼花朵朵相继,真就像它的另一个名字——一丈红,咄咄地生出丈许开外,越是爬到高处,越是红得耀眼。喃燕很开心,小小年纪,竟知道爱花,掰弯了秆儿采来戴在头上,别在襟上,臭美得不行。她又帮梅燕打扮,两个小人儿穿戴得花姑娘似的在院子里疯跑,惹得大人都笑。老阿姨说,小燕子,你别带着大燕子到处乱跑,当心摔着。喃燕就撇着小嘴说,不摔,就跑。老阿姨没辙,随她们闹去,那边又有孩子拉了一裤兜儿,她可没闲心跟个小丫头打嘴仗。
到了半下午,喃燕跑得没劲儿了,忽然感到一阵忧伤。真是奇怪,这小鬼恐怕不知道自己有着怎样的情绪体验,总之她感觉没劲儿透了,盛开的蜀葵花也不能让她开心,小小的腔子里,有细细柔柔、曲曲弯弯的丝线样的东西,不惹人注意地悄悄爬出来,一下子让她失去了对活泼世界的兴趣。她踢着脚底下已经发蔫的蜀葵花,自言自语地说,燕燕,想妈妈了。梅燕还在一旁憨头憨脑地笑,好像这世界没有什么是使她不满意的,上午的疙瘩汤、下午的磨牙饼、老阿姨的唠叨甚至呵斥,全都使她满意,她因此笑得天真无邪。
梅燕,走,找妈妈。喃燕拉住梅燕的手。
知了藏在梧桐树上,它说,知——了。梅燕清澈的大眼睛里没有丝毫犹疑,既然喃燕拉住了她的手。
就这样,两个小把戏,一个一岁半,一个两岁,手拉手走在托儿所通往轧钢车间的路上。她们要去找妈妈。
这一路可是漫长得很,夏天的云都倦了似的堆在天边上,一朵一朵的棉花糖,软绵绵的毫无气力,但是两个小人儿心里又快活又勇敢,充满了探险的趣味。这条路,妈抱着喃燕走过可不止一回,到底有多少回,喃燕都记不清了,反正趟数不少,小而坚决的印象里,妈总是奔忙在轧钢车间和托儿所之间的这条路上。有时抱着她,有时背着她,有时一手拿着饭缸子,一手托着她的屁股,有时腰上挎着装尿布、米粉的背包,胸前还挂着她的小水壶,反正妈不是一个人,妈纤瘦的身体上,像长出一个器官似的,挂着小喃燕。
路过三食堂,喃燕指给梅燕看,包子,米饭,面条。她说的几样,梅燕都吃过,因而点头同意。喃燕又说,花菜烧肉,鱼头豆腐,梅燕就不知道了,只好摇摇头。这些菜就连大人也不常吃呢,梅燕妈从没给梅燕买过。但喃燕妈给喃燕喂过肉汤和鱼汤,花菜嚼得稀烂,鱼肉呢,先剔掉刺儿,再往嘴里趟一遍,细细地喂给喃燕。喃燕的嘴因此也比梅燕刁些,老阿姨喂的粥不肯吃,非等她妈来了,才张嘴。
又路过幼儿园和子弟小学,学生们都放假了,校园里静悄悄的。喃燕妈抱着喃燕路过这里的时候,咿咿呀呀地和喃燕说过,再大一点儿,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再再大一点儿,就可以上小学了。喃燕知道以后会来这里,就往小学校那边望了好几眼。她看到一个大象鼻子滑滑梯,还看到并排的三个秋千架子,连挂秋千的麻花铁链子都瞧得清清楚楚。可惜学校大门锁着,进不去。
又走过一堆散放在草丛里的钢锭,小蝴蝶从草窠深处飞出来,绕着她的花裙子翩翩起舞。她居然还记得,这时候要拐弯儿。她停下来,指指右面,说,那边,妈妈;又指指左面,说,那边,大门。意思是向右拐能找到妈妈,向左拐可就错了,那是钢厂的西大门,再走就上街了。分不清左右,但知道“那边”和“那边”不一样。梅燕当然是听她的,两人拉着手,摇摇摆摆地往右走。
走了一会儿,看见工地上正在盖大楼。那是厂里新盖的办公楼,据说盖起来有五六层高,可气派了,连厂领导都佩服自己的大手笔。可两个小人儿不管这个,喃燕对梅燕顺嘴说,盖大楼。梅燕没吱声,也就过去了。那座大楼现在还没什么眉目,不比厂房高多少,确实没什么值得两个小丫头注意的。
夏天的风景真好,梅燕撅了一支狗尾巴草,笑呵呵地拿给喃燕看。喃燕推掉梅燕送上来的狗尾巴草,说,花好看。梅燕就把狗尾巴草扔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朵蔫头耷脑的蜀葵花来。蜀葵花皱巴巴的,早没了鲜艳的模样,喃燕学着大人的样儿,叹口气说,花谢了。梅燕看看手里的花,嗯了一声,不知道该扔还是不该扔。喃燕把花接过来,走到路边草丛里,使劲儿一丢,花“咻”地跌进蒿草深处去了。
喃燕回过头来,满意地对梅燕说,花睡觉,明天好看。
梅燕就懂了,知道花也累了,茂密的青草地是它的床。
两人接着找妈妈。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许有一岁那么久吧,也许有两岁那么久吧,她们终于看到了妈妈。先看到的是梅燕妈,她在车间门口和主任说话,忽然看到自己女儿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吓了一跳。车间主任揉揉眼睛说,我没看错吧,这俩小鬼怎么找到这儿的?接着就有人跑去叫喃燕妈,哎呀,小徐,你快看看去吧,你女儿带着梅燕来找你啦。
喃燕妈着急忙慌地往门口跑,看见车间主任背着手,正弯腰跟喃燕说话呢。
你找妈妈来了?花白的头颅抵在小苹果似的嫩脸前,一本正经地问。
嗯。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在上班?
嗯。
那你还来?
想妈妈。
想妈妈也不能来。
为什么?
你妈妈在上班。
燕燕想妈妈。
想妈妈也不能来。
为什么?
你妈妈在上班。
就想妈妈。
一老一小说着车轱辘话,简直能把人笑死。
看见妈过来,喃燕憋得通红的小脸松了口气,赶紧往妈的腿肚子底下钻。从腿缝儿里,她偷看那个找碴儿的老头儿。老头儿也正在看他,被褶子皮挡住半拉的小眼睛一闪一闪的,打着节拍似的点着花白脑袋,似笑非笑地说,小燕子,我跟你说,以后不准到车间来,要是再来,我就扣你妈的工资。还有你,大燕子。他转过身去找梅燕,以后不准跟着小燕子来车间,听到没有?
梅燕不知道怕,站在她妈身边傻乎乎地笑,好像老头儿说什么都跟她没关系。喃燕却委屈死了,抱着妈的腿儿不撒手。她生气,把自己气得小脸通红。小嘴儿噘着,不吭声也不吭气,妈哄了她好一会儿,她才让妈把她抱在腿上,用小勺喂着吃了半个苹果。
另外半个苹果给了梅燕。梅燕吃得不费劲儿,她的牙都出齐了。
这件事还不算完,喃燕知道自己可以从托儿所溜出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这激发了她极大的兴趣,肥胖颟顸的老阿姨越发管不住她,动辄气得拍着大腿虚张声势地喊,小燕子,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就叫你妈把你领家去。她才不怕呢,领家去,正好可以黏在妈身上啦。可是,又有一种新的雀跃的心情让她离妈远了那么一些,是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她不是很明白,只知道不可以去车间,妈在车间里,她不能去找妈,却可以走出托儿所,离妈近一些。那么究竟是远一些还是近一些呢?这问题她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想往外跑。
有一次,她和梅燕差点儿都走出西大门了,让门卫给拦下来,瞧西洋镜似的咂着嘴说,这谁家的孩子?喃燕仰头说,小徐家的。门卫抓下帽子攥在手里直呼扇,笑呵呵地说,哟,胆儿挺大呀,让你妈来领人,不给一包烟,不让走。喃燕噘起小嘴儿,奶凶奶凶地说,就不给。
妈后来到底还是给门卫塞了一包烟,喃燕亲眼看见的,从此后晓得也不往西大门走。
不能去车间,也不能走出西大门,但总有地方去。
夏天是很快活的,蜀葵疯长,草也长得疯,有些杂草没膝的地方,喃燕和梅燕跳进去,就看不见了。她们的小辫子上沾满草籽,像顶着一头怀孕的草。蝴蝶和蜜蜂在她们的鼻子前飞过去,又飞回来,像绕着两朵花转似的。她们还跟那些大孩子们一起,在钢锭上爬上爬下,仿佛在巨大的钢琴上踩着琴键,哆来咪发唆拉西,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妈给喃燕唱的歌,喃燕记得可清楚啦,哼起来居然也像模像样。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雨水多得很,可是春天还在,躲在花蕊里、草尖儿上、树荫后、小燕子的尾巴上。
那些大孩子可瞧不上她们这样的小丫头,但有什么关系呢,她们并不在乎,跟在后面去工地边上捡小石头,或者把瓦楞纸盒子翻过来,搭成小房子。梅燕口袋里总是装着喃燕摘给她的蜀葵花。喃燕摘了就忘了,梅燕却忘不了,她把蜀葵花装在衣兜里,左面的和右面的衣兜都装满了。
夏天的蜀葵可真好看,到了晚上,梅燕就把兜里的蜀葵花都放回草丛深处去睡觉。如果喃燕给了她三朵,她就放三朵;如果给了五朵,就放五朵。她说话不大利索,对数字却有好记性。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保证不会出错。
这天大孩子们新找到一处好玩的地方,她们跟在后面,一点儿也不害怕。老阿姨的话是不必听的,妈的话,得听,但也不是回回都听,因为妈不让喃燕去车间,也不让喃燕出西大门,所以喃燕就认为,前两次都没去对地方,这一回,她趁着老阿姨和人说闲话的工夫,偷偷带梅燕溜出来,不去车间,也不去西大门,就在广阔天地里玩儿。早晚她和那些大孩子们一样,不用上托儿所,到了夏天就放假疯玩儿,这样才快活哩。
前段儿下雨,工地停了工,孩子们就趁机溜进去,找到一个不大的水坑。那坑也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或许只是一个坑,原先是没有水的,下了雨,就积成了水坑,看起来有边有角,四四方方的一块儿,像谁切的豆腐。大孩子们从旁边抬过来一条木板,搭在坑上,蛮像样儿的一座“桥”就搭成了。这独木桥招孩子稀罕,他们一个个从上面走过去,伸出两只细长的胳膊,做出夸张的造型,好让自己保持平衡——其实好好走路就成,他们偏不,偏要摇摇摆摆的,好像走过“桥”去是多么困难、多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看得喃燕心里痒痒的,雀跃地也要上去。大孩子们自然不让,往边上轰她,去去去,别掉下去。
大孩子们玩了一阵儿就到别处寻开心去了,这游戏远不能满足他们新鲜的追求。喃燕看他们走开,觉得机会来了,就摇摇摆摆地走到“桥”边上,伸出一只脚,摇摇摆摆地踏上去。梅燕也不晓得拦,她没那个觉悟,倒满是好奇,想瞧瞧喃燕有没有本事像大孩子那样走过去。要是换作她,她是不敢的,但喃燕胆子大,喃燕还聪明,总能干成她干不了的事儿,因此她乖乖地站在一旁,眼睛里放着光,看喃燕扎煞着两只小手,像那些大孩子似的,学鸟儿那样张开翅膀。
喃燕走路稳,大人都夸。梅燕虽年长几个月,走路还不如喃燕稳呢。
喃燕也蛮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走过去。
要是她不学大孩子那样摇摇摆摆的就好了。偏她学得像,好像不摇摆就不能算是走独木桥似的。
她伸出细细的胳膊,花裙子的泡泡袖就耸起两个滑稽的大馒头,把她的小脑袋夹在中间,让梅燕咯咯笑出声来。喃燕不笑,她可认真了,胳膊伸得笔直,连摇摆的幅度都模仿得一丝不苟。她的白色塑料小凉鞋踩在“桥”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慢腾腾的,像是电影画面里的慢动作,小花裙下裹着的娇小的身体却越来越厉害地晃来晃去,让人倒抽一口凉气。要是有大人路过,看到这场面,一准吓坏了,可喃燕过“桥”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样子,只有梅燕看见了。
梅燕看见喃燕顺利地走上“桥”,又顺利地走下“桥”,可高兴了,她也想试试。她摇摇摆摆地走到“桥”边上,伸出一只脚,摇摇摆摆地踏上去,又扎煞起两只小手,像喃燕那样学着鸟儿张开翅膀……
往后的事,喃燕就记不住了。
其实前面那些,她大概也没记住,谁也不记得自己一两岁时候的事。那些都是妈后来告诉她的。
妈说起她小时候的事就叹气,妈说不记得也是对的,小小年纪,吓坏了,直嚷嚷“我掉到大海里去了,我掉到大海里去了”。为这,梅燕妈还宽慰喃燕妈,会好的,小燕子福大命大。
那天之后,喃燕就病了,高烧,说胡话,烧得狠了还抽筋,可给喃燕妈吓坏了。到厂里医务室扎了针,拿了药,也不见好,又去市里医院瞧。市医院的医生说,转肺炎了,得住院。市里医院到底条件好得多,果然治好了,可落下个毛病,喃燕听不见了。妈问为什么,市医院的医生说,别问我,送来我们这儿之前,你们是怎么治的?妈老老实实说,就在厂里医务室,扎针,吃药。医生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说,那就是这个原因了。
妈欲哭无泪,厂里医务室的聂医生人不错,喃燕每回生病,都找他。不能因为市医院的医生一句话,就赖聂医生把喃燕给治坏了。可是不赖聂医生,赖谁呢?市医院说反正不赖他们,他们救死扶伤,那么多危重病人都治好了,论经验、论技术,这种低级错误是绝对不会犯的。妈期期艾艾,说不出话,就只好认了,只有赖自家的命不好。
其实也不能赖命,若说命不好,梅燕家更悲惨些。好好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谁想得到呢,就为捡一朵花——梅燕摇摇晃晃过“桥”的时候,口袋里的蜀葵花掉出来,飘在浑浊的积水上,漾出另一朵更大的花。
后来大人找过去,只找见水坑边上大哭不止的喃燕。问她,只是哭。我掉到大海里去了,我掉到大海里去了!她哭着喊。好像除了哭,没有别的事再让她感到人生的兴趣了。有细心的人发现水坑里细细地漂着几根头发,一把抓下去,这才把梅燕捞上来,可是小脸煞白,小小的身体早已凉透了。根据漂在水面上的那朵蜀葵花推断,孩子应该是弯腰捡拾的时候不慎从木板上跌落水坑的。
妈把哇哇大哭的喃燕搂在怀里,自己也受了惊吓似的跟着哭。车间主任劝她,小徐,孩子找到了就好。妈听不见,还是哭。车间主任见劝不住,也就不劝了。梅燕妈已经哭得晕了过去,车间主任只好指挥众人先把小凌弄去医务室。
打那以后,喃燕妈和梅燕妈这对好朋友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那膜薄薄的,说不清道不明,伸伸指头就可以戳破,但没人愿意戳它。如果喃燕妈跟车间主任临时请个半小时的假,说,主任,我去托儿所看看女儿。必得小心躲着梅燕妈。如果梅燕妈看到喃燕妈抱着喃燕走过来呢,就会生出带着钩子的眼神,像是看着什么稀世的宝贝似的,直到母女俩走得远了,还能感受到如芒在背的眼光。那眼光,唉,让喃燕妈思来想去,终于还是提出了调动工作的申请。
喃燕一岁的时候就能说会道了,到了两岁,却不会说话了。听力问题影响了她的语言能力,妈心里难受,可也不得不接受这份“惩罚”。算是惩罚吧,妈的想法不得要领,可如果不是老天爷的惩罚,那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怎么就突然听不见了呢?妈流了一澡盆子眼泪,想把喃燕洗干净。可是,不够,女儿终是听不见。妈就想,她的眼泪起码要流满那年工地上那个吃孩子的水坑——梅燕爸后来特意拿了根一人来高的竹竿去水坑那边试探过,一竿子插下去,只留了不到十公分在水面上,就是说,即便是成年人掉下去,也打不到底哩。梅燕妈哭惨了,她说要是她的眼泪能换回女儿,她宁愿把自己哭瞎。
那个夏天,到底是忍着入骨入髓的痛熬过去了。
再往下,日子也就没那么难过,一转眼,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合城钢厂都成了历史,得在地方志里才能找得到。找到也没意思,不过是时代大潮的一个陈旧符号,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消亡了也就消亡了,就像一个春天轮回另一个春天,一个生命替代另一个生命。
喃燕现在也到了不惑之年,岂止是不惑,简直是通透。现在她在特殊学校教手语,轻易不开口说话。所谓金口难开,恐怕就是她这个样子了。看什么都顺眼,也就不必开口,像是修到了一定的道行,只剩下慈悲心,遇到什么,就拈花一笑。在此之前,她从未听妈说过四十年前的那段往事。可能,妈认为不必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让大人难堪,也让孩子背上不必要的包袱。当年妈调出钢厂之后,不久爸那边也分了房,回城坐上了办公室,真是皆大欢喜。要说有什么心病,那就是喃燕了。可一想到同是当妈的小凌,妈又打心眼儿里觉得老天爷待她不薄,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除了听不见,说话少,喃燕一点儿也不比别家孩子差,她照样是聪明的,灵巧的,可爱的,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扑闪扑闪,漂亮得不像话。旁人不知情,看到这双会说话的眼睛,还以为她天生就不必开口说话,有什么好东西,不用她说,人都肯给。这种表面上的满足,妈也是感激的。
直到今年春上,妈去社区诊所开高血压药,竟遇上了四十年没见的梅燕妈。
起初不敢认,四十年啊,多经久的花都开败了,要不是就在眼面前,谁也想不到从少妇到老妪,能变成什么样儿。后来还是梅燕妈从喃燕妈的口音里听出一点儿名堂,就问,你老家是S县的吧?喃燕妈说,是哎,乡音难改,到合城四十多年了,还没变过来呢。梅燕妈就说,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S县的,她人可好了,会钩针,什么样的稀罕花色都会钩。她给我女儿钩的小衣裳、小裙子,真是漂亮,我一直舍不得丢。你瞧,就是现在,穿在我孙女身上,也一点儿不过时。喃燕妈这才仔细打量眼前这个老太太,越瞧,越觉得眼热,再打眼瞧瞧老太太身边的小女孩,一岁多两岁不到的年纪,扎个小辫儿,唇红齿白的,差点儿失声叫起来,这不是梅燕那个小姑娘又是谁!
喃燕妈捂着嘴,不敢相信似的问一句,小凌?
老太太就笑起来,我说嘛,怎么这么像!
两个老太太赶紧拉着手,找地方聊开了。那长得极像梅燕的小姑娘十分乖巧,偎着她奶奶,自顾玩一个闪光的球,半天不动弹,像是没有大人在身边一样,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喃燕妈就叹,和梅燕一个脾气,长得也像。梅燕妈说可不是嘛,我疼她,也像疼梅燕一样。两人唏嘘了一阵,时光都在不经意中溜走了。
回到家,妈和喃燕比画着说起当年的梅燕。这是第一次,妈敢在喃燕面前提起梅燕。但好像喃燕并不感到意外,她点点头,看穿了时光的云翳似的,悠悠地说,我记得——
因为常年难得开口,她说话的声调很奇怪,像是一颗裹着糖浆的石子掉进水瓮里,激起沉闷而甜腻的回声。

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一级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两百万字,多部作品被权威文学选刊转载或收入全国重要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雪落西门》、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个人专著。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