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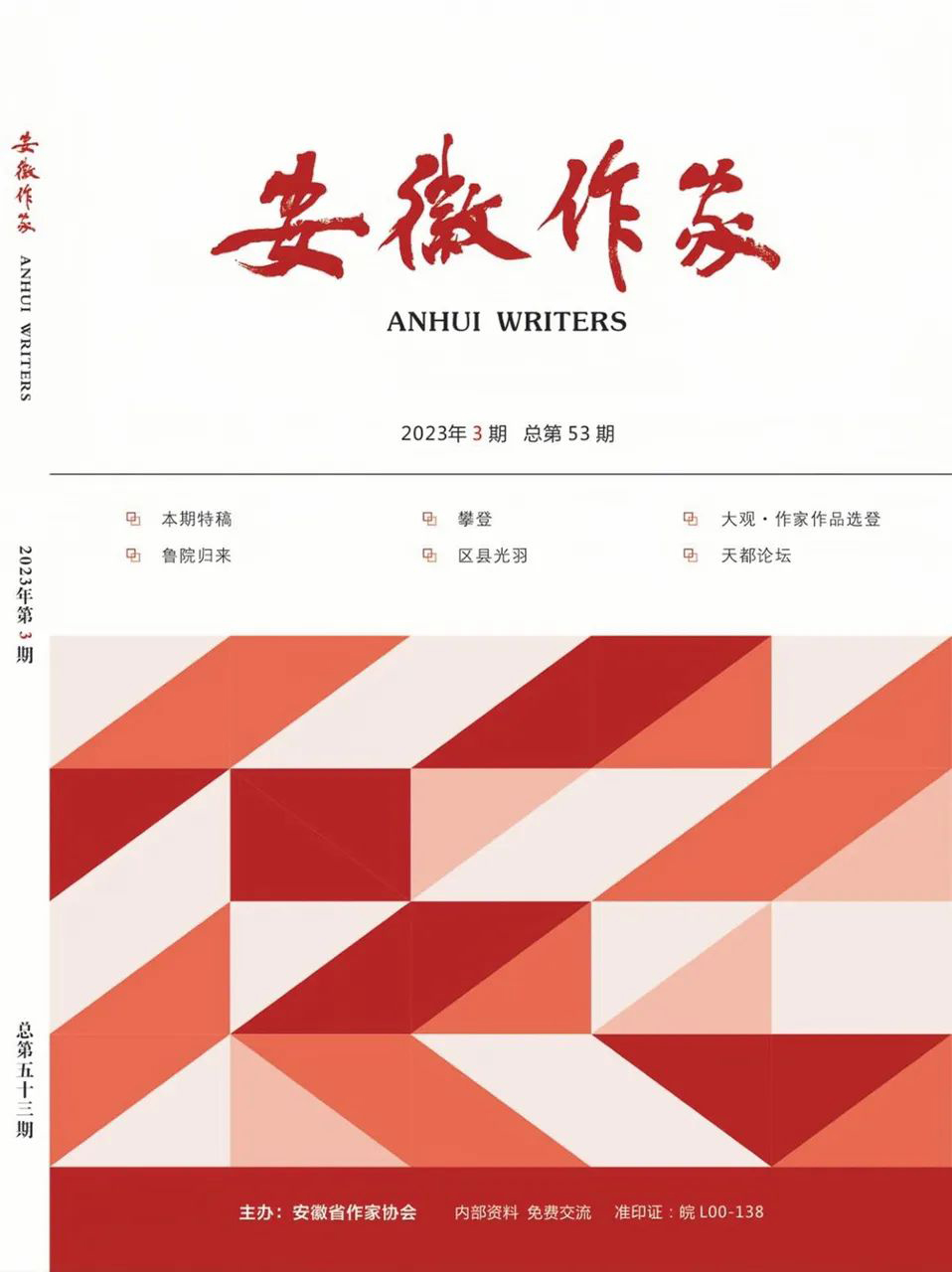
作品欣赏
生 烟(节选)
黄亚明
盆地
昨夜我梦见古皖之地的冶溪镇,阔美、润圆,周遭无边荡荡的山峦、森林、悬崖似要倾扑擒伏——雨滴的音符铮铮绿亮,而法术的野兽、山妖、神仙以游鱼出没不定之势,集体调整着暗黑中的身姿与呼吸。荆棘山道逼仄崎岖,月光啁啾,铺满银杏、古槠、香樟、枫香、紫柳、桂花,恍若舞衣锦绣斑斓,沿山而上,又是山鬼似的寂寂杉木、柳杉、马尾松、栓皮栎、青冈栎、黄檀层层包抄,围拥出驳杂奢侈、闪闪发光的扁头鲢一样腥凉的气息……一个吴楚过渡地貌的清脆盆地,以盛放父性的初生山水为荣耀,是母性之硕大红盆的虚幻呈现和沉陷,亦是插秧伐薪采茶农人的劳绩之所。圆拱如月的卷蓬桥下,人影树影桥影花影相扶,人家墙角去年的南瓜如此浑圆,令人耽溺,像桥边永不可醒来的古老原野梦境:忧郁胶着的阳光如同红绿奔腾的雨水,持续灌入荒田里一匹睡卧的黑牛体内并嗡嗡晴响。
庚子年三月二十日,西方传统的复活节,我在一马平川的冶溪镇晃荡。按照网上万年历所言该日宜祭祀、祈福、开光、求嗣、斋蘸、纳采、订盟,忌开市、动土、掘井、开池。四野鸟儿发情,群群蜜蜂茫然得不知所向。广漠田畴的油菜花或开或谢,半开半谢,渐渐粗实隆起的茎干,如同女巫的绿色权杖悬垂膨胀的松果,溅起松烟阵阵——万物的枝条像一首叙事长诗,溢出了处处肥沃的山地雌性美学体系。
山中小盆地多有未名之美,人性之力,本心之爱,以及未名之美里永难言说的致命清新——
亦南亦北,冶溪乃女性古中国积雪映白的情意别册,在太湖、岳西、英山三县的结合部,浸润稻米之乡的妖娆和慈祥。摩托轰响,小车突突,沿地跨鄂豫皖三省四市的大别山南麓攀援,北达古寿州、舒州(一部分隶属皖西六安市),飘散霍山黄芽、六安瓜片的迷魂之香……西抵湖北黄冈,交杂板栗、酥糖、挑花、老米酒和甜柿湿漉漉而安静的晨梦……西北远赴河南信阳,与固始鸡、鲌鱼、麻花、高桩馍、商天麻、神仙饺在锅碗和药罐之间摇荡……而这里如许众多的森森古木,朴素深褐的千百年木纹上,闪过新石器、殷商老器、犁耙、插秧机和大棚石斛的熹光,本色,自然,劳作,轮回,镌刻着生而为人的温憨和忍耐。
沿街漫走,翠光荡漾的茶叶、黄泥腌裹的鸭蛋、舞灯人、说书人、橡栗子豆腐、烤得半干的焦黄小河鱼、河汊的米虾,一种浓郁的菜市场属性的叫卖声,充满家常和市井的微妙和凌厉,是腌臜的、粗鄙的、块儿八角的,也是热烈的、喧闹的、生机勃勃的。
——清超幽迥、又怅惘难以为怀的绿国,灼烫为峰顶、天空、稠密的枝杈、破旧祠堂,以及黑发少年暗红发芽的情思。
长河之上
少年时我一度误将冶溪河听成野鸡河,她美野美艳像澎湃的校花令人孤单乏力。野鸡的含义昼夜充满古怪忧伤的暗示:野鸡,雉也,雄者冠红尾艳华衣雄服。野鸡亦是我乡对随性女人的蔑称,事实上雌雉虽娇小却尾短,羽毛灰褐——但一提到野鸡,蔑视的男人常常双眸火星放亮似厨中的菜籽油欲倾浇而下。“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先秦无名氏《雄雉》),叫得那么欢实是唱给谁的颂歌?冶溪河我二十余年来过七八十次,沿河的鸟叫(也包括雉鸡的求偶之音?)一向如糯米白粉撒下安抚人心的阴凉,几百棵老枫杨枝遒叶绿晃动使人迹近失明……今日是六点钟的黎明,往昔激壮的河水已被深雾笼罩,水流以及枫杨、垂柳与天地一体凝滞,影影绰绰中像人间暮晚的街道突兀起无数买卖牲口的摊铺,各种各类各条各个各界的兽色或褐黑或泛青,在等待诡异的山精或诚恳的麦穗来挑选认领。我真的听到了新麦香,勾了魂似的从天空的漏斗里一丝不苟地漏下来,并被时间和深雾减损了几分。当油光细滑的阳光被东面的司空山从云缝中拎出来时,一切变得像与熟悉的邻居即兴攀谈,他们携带着睡眠的温热陆续行走在巨阔的田畴料理农事。水气因此绵绵消散,清亮的水光晃映上岸边;茶农耷拉着猩红的睡眼将熬夜赶制的新茶送往河对面的集市;远处的东方红水库沉淀一夜的绿会开始一天之中的第一次漾动;联庆村一进七重的清代祠堂正在修整,门前冠盖如巨伞的枫杨上(春风吹荡树下荒凉坟包上的塑料红花和黄裱纸,一枝映山红在旁边兀自新鲜怒放),静悬的晶亮露珠业已滚溅一地,就像我不能踏进同一条冶溪河。这就是生命燃烧的源头,长江支流皖河的支流长河的一级支流之一——冶溪河醒来的翠绿情形。隔壁翻过马踏岭是我的血脉故乡黄泥坡。我用手丈量地图,她发源于皖鄂交界的西坪村,离黄泥坡十多里,流经联庆、桃阳等民居村落,在梅子林入太湖县境,至潜山县与怀宁县交界的石牌镇汇合皖水、潜水形成皖河干流。长河之上,自源头至狮子岩六公里的上游段,坡降达45‰,狮子岩以下,坡降为8.4‰,所呈现的锐角和山势相依。这么多微小的泉水噼啪汇聚,一路奔突裹挟两岸的徽剧、黄梅戏、岳西高腔、潜山琴书、太湖曲子戏和孔雀东南飞的传说,像酒坛被众多的酒仙加冕,之后从安庆步入长江温软的怀抱。我觉得她是一支少女挥动的山楂树的手臂,羞涩,沸腾,充满陌生的、原始的、农业的质感。我叫她冶溪,或者野溪,在野之溪,清声亮彻,构成“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式的……汁甜液美的花木中国,迷途知返……
温泉册页(节选)
冯润青
坐在一块来自洪荒时代的石头上遐想
一回头,山下的稻田,金色的地毯,平铺直叙地闯进眼帘。
它们起伏着,燃烧着,涌动着。
坐在一块来自洪荒时代的石头上,身前是树,身后是树,左面是山,右面是山。山风带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如波涛一样,一叠一叠地闯进耳朵。
这是温泉镇东营村,村后是绣花尖。
绣花,一个文文静静的名字。
绣花尖前的山岗上,有一块石头。形态如石轿,人们叫它轿子石。关于轿子石,民间流传一则故事。
情节不一定多么跌宕,但故事里有善良和丑陋,有正面、反面,符合大众对真善美最直观直白的向往和崇尚。——恶魔终于被正义打败,他乘坐的轿子落地化为石轿,永远嵌在山岗上,经年累月接受风雨雷电洗礼。
山路迢迢。上山的路,从农家屋角拐过,沿着山脊蜿蜒向上,穿过茶叶地,穿过一些杂草、一些高高低低的树。
那里一株蓝色的牵牛花在光影里躲躲藏藏。与朋友讨论蓝色牵牛花和红色牵牛花,不约而同地对蓝色牵牛花多些些好评。
“蓝色牵牛花有气质。”“清冷、高雅。”
每个人的性情投射进物的好恶,看似没有道理,实则有迹可循。
狗尾巴草如同被岁月熏染的老汉,深深地弯下褐色的穗子;冬瓜在阔大的叶子下伸头探脑,其间纤毛绒绒的小瓜头尚且不懂秋剑相逼的残酷,依旧保持着童贞模样;地边月亮菜随意攀附些些高枝,紫色绿色的月亮一朵朵童话样缀在藤蔓上,闹腾得欢;橡子树枝头结着自带小碗的橡籽;蚱蜢突然从草丛里蹦出来,虚张声势后逃之夭夭。
这些悠悠荡荡的小美好,这些隐秘又张扬的小物事,如同秋日的阳光,蓝天上的白云,让人忘记时光里的皱褶、尘埃里的沟壑。
然而,多么轻。坐在轿子石上,不被它赋予的故事侵扰,让思绪翩然,轻轻。
隐藏入时光深处的东西二营
流淌的东营河依然自西向东,沉默着,悠然着。它不曾寄去历史长河中依附在它两岸的人,或者马、牛羊,又或者一只雀子,一只蚱蜢,亦或一花一叶,一草一木。
曾经,这河两岸,驻扎过两座军营。每天,马嚣人闹,喊声震天。那时候,这个山湾湾里有很多梦。以梦为马。马上江山,马下农耕,多么丰富的向往,多么纯净的旋律。
从几百年前祖祖辈辈流传下的那些记忆,东营河也不曾寄去。时间长河流淌的远方,空间能抵达的远方,所有结局和未结局的远方,可曾期盼一封信甚或一片寄语?
或者,这条东营河记得。记得山河遥遥,岁月沧桑,人事苍茫。
公元三世纪前期,魏国曹操率大兵征伐东吴,在此驻军练兵。
军营里人和马一同饮过此河的水,一同吹过此间的风。
且以河为界,一东一西。河东唤作东营,河西唤作西营。山青了又黄了,山丰了又瘦了。曾经的东西二营,从时空中拔营而起,开赴更深更远的时空。
东营村,却留了下来。
军队走了,村民占地而居。仿如耕地上没人侍弄、作物不长时,很快野草丛生。人类和野草,本质上是一样的。
东营村四面环山,仅东南方有一河口出入,村内土地平旷。三国时,此地易守难攻,又兼可跑马练兵。曹公言,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东营村有些地方名称,仍保留有军营色彩,如大牢湾、马练岗、旧营畈等。“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也是东营河两岸的写意呵。
那条东营河,在秋阳中泛着泠泠的,细碎的银光,清清亮亮地站在一圈山岗的怀抱里,恬静,安然,依旧不闻不问两岸的汲取,依旧默默吐出生机、希望和芬芳。
河流始终比时间流淌得慢而从容。
……
老屋:光阴厚朴(节选)
刘捍华
一
去皖西南,去岳西县五河镇小河南村。
小河南,小河之南,时光之里山北水南,你我之间人来人往,于熙熙攘攘中,遇见一片厚朴光阴,仿佛遇见春天的笑容向我走近,阳光的语言在心里回荡。
居易以俟,光阴荟聚。李冲花屋、凹上老屋托举着三十六度的太阳,托举着碧空白云,沉静而缓慢。四周的青山,已是勃然,已是情深,骨骼清奇,双臂围抱,把这两座老屋紧紧拢在怀里。
我从不掩饰对老屋的热爱,从不掩饰对古朴光阴的流连,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里住着一栋又一栋老屋。去过银河村的光岩老屋,经过前河村的筏形老屋,也赏过北山村的岳红四合院,我曾都以安静之名,致以纯粹的喜爱。其实不够,远远不够。在李冲,在凹上,心间又流淌出一个词:村气。
村气缘于李冲、凹上老屋的体系,博大庞然,时光、农谚、摇篮曲、月光谣、醉酒后的胡言乱语,甚至生与死的契约,都写在这里,写在这一片光阴里。村气不是市气,不是官气,也不是市侩气,它是乡村特有的气息,是穿弄绕堂的风声,是雨滴敲击青瓦的曲音,是扶直炊烟的岁月,是老屋里的人声鼎沸,是阿公阿婆的呼唤,是历经漂泊之后的咂摸……
阳光推搡我们走进老屋。穿过一个又一个天井,经过一条又一条弄堂,走过一间又一间堂轩和厢房,恍如烟海,恍如书卷,恍如一筒黄烟经过肺腑。老屋完好,岁月无恙。大部分房间都是空闲的,偶住几个老人,他们坐在天井旁、阳沟边,太阳照在青瓦上,泛不起一丝波浪,凉沁的风从大门小门钻进,一下子消失在墙壁的罅隙里,隐匿在我们的身体里。
门外,窗外,阳光在喊。其实,村气自带阳光的烈性和香气。阳光打在斑驳青砖墙、泥土墙上,打在青瓦、马头墙上,没有声响。我四处张望,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回来了,牛羊进圈,鸡豚入笼,孩子放学,大人收工……仿佛所有的场景都回来了,碓臼在动,石磨在转,蒸笼冒热气,火塘上的熏肉散发着陈香……
李冲、凹上老屋庞然,盛时二三十家,自然有着充沛的村气。村气,其实就是人气,是人在老屋里生长的痕迹,是岁月里最恒久的雕刻。腌菜的气味、猪圈鸡舍的气味、草木灰的焦味、牲畜粪便的酸臭味、田间稻谷的香味、缸里新米的清味、米糟发酵的甜味、儿女游戏的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跳脚痛骂,红白喜事的忙碌穿梭和醉倒,除夕夜的串门辞年……一切的一切,都是村气。
唯有老屋,蓄积了无数的村气。村气的熏染,使得生活、命运、人生经得起摔打,受得了风霜,忍得了冷眼……那群肤色黝黑、骨骼耸立、经脉粗壮的人去了哪里,光阴沉默,老屋不老。
——仿佛走了很远,现在却迷路了。
你不信,你的语气碰撞阳光,
我们一再用来下酒的这个词,
是少年的猫耳刺。你信了,你说,
离得越远,疼痛就越尖锐。
我说,把这个词一笔一画拆开吧,
整个上午,我们一遍又一遍拆解,
风吹着青山、白云和斜阳,
我们把这个词,拆成了唯一的去向。
二
时光凌厉,又不动声色;铅华洗尽,又回声温暖。
缓慢穿行在李冲、凹上老屋,好像穿行在历史的旧痕里,行走在过去的时态里,悠然在掌故的脉络里。
岁月剥蚀,当年的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渐渐隐去,天井上,青瓦上,白云一片,似乎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厚朴光阴之下,驳墙青瓦之上,习惯生长碧空、洁云、雨滴、雪花,以及一层一层的风霜。不同的是,墙上缝间,也生长了些芜草蛛丝,阳光下,又古老又清新,让人又惊喜又沉重。
不论是李冲花屋,还是凹上老屋,都是精巧又粗犷的,大写意里藏着小精致,具象里面藏有抽象,内涵之内又有着敞开的外延。比如李冲花屋,以五个堂轩为中心,向左右前后长驱直入地辐射,形成一个三千平方的超然“博物馆”。博物馆是无数光阴的荟聚之地,是文化在光阴中沉醉、积淀的密码。
文化的幽香,不是一年两年积攒的,它必得经过岁月的酝酿,才会发出真朴之味。李冲花屋官厅中门门楣砖雕精美,刻有“居易以俟”四字,有哲学的意味,也有生活的智慧。《中庸》有言,“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有一种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况味,也有一种素位而行无不自得、居易以俟乐在其中的豁达。
刘基在《旅兴》诗中云,“论年未应尔,胡为遽如期。大块播万形,一躯非我私。暂假终必还,但有速与迟。居易以俟命,圣言岂吾欺”,也是一派千帆阅过的通达。心守乌云,则居大不易;心如明月,则穷达不拘。拨开乌云见明月,明月照我俗世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论穷达,都固守本心。这是古人的智慧,是古民居的智慧,也是我们不断放弃的智慧。
智慧的底色,和李冲、凹上老屋的底色相同,风雨侵蚀着民居,却始终冲刷不掉我们的向往,却始终不能让我们放弃归途。对我们来说,从初心回到初心,从村居回到村居,从底色回到底色,中间只是出了一趟远门,一场热闹訇然过后,世界归于平静,老屋上空开满了白云,一切安宁、平和、冷静而自由。其实,这底色就是简单、归真,听从内心。
这是古人的生存哲学,也是一切草木、牛羊和人类的生存智慧。
凹上老屋的体量稍小,却有着另外一种格局。第一感觉是高大,门楼高,崇尚河南的高门大院。我曾路过河南,不论贫富,家家户户皆是门楼高高,两层楼高,大概是中原文化的傲气使然。凹上老屋的门楼也有两层楼高,官宦世家,门前两石,分别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应是官威赫然,官声沛然。如今,只剩一片静然,大浪淘尽风流,山水引出璞真。堂内悬挂两匾,其实是三块,我感兴趣的是其中两块,一块“淳厚遗乡”,一块“学彻玑衡”,声高而仁厚,学深而精进,不骄不奢,不言不语,却自有一种威仪。玑衡泛指天文历法,我猜,隐居凹上的官员,应是天师、国师,受人尊敬,才会有人自觉下轿下马。
居易以俟,淳厚遗乡,一派长者风范。白居易《村居》诗云,“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萧条尽日风。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经过多少沧桑,归来依然平和安然。老屋是长者,经过光阴、人生、文化的浸润,呈现出斑驳、通透的色彩。
——我们化身一首诗歌,侧身挤进来,你说,有些地方,只有诗歌能去,只有镰刀能去。镰刀收割白云,收割幽香,开门把寂静放进庭院。老屋足以容纳我们的苍茫,所有的坑坑洼洼,在远处低了下来。我说,总要面对来自黑暗的一个词,总要头顶风霜,身披樟树和朝阳。
……
南朝梦忆
余敏轩
从煦园出来,途径六朝博物馆,决定进去看看。大门题字,一看即知是集的王羲之,用书圣的字,很合适。两处相隔不过几百米,沿街慢行,也就从明初走到了魏晋。今日连绵的细雨,一片朦胧中,远处高楼若隐若现,像极了南朝的岁月。
自感与这座六朝古都的缘分是深的,这座城市有很多的名字,但我还是更喜欢叫他金陵,或者建康。记得好友青夏来金陵相访,是夜为我写下一张小尺幅。“相遇金陵,一生健康”,字极俊美,语义精妙,可谓一语双关。
闲时曾遍访此地六朝遗迹,石头城的江水早已退至几公里外,台城的烟柳依旧迷蒙,周颙隐居的钟山,偶尔也能看到人家在院内开辟的一小块菜地,种上春韭秋菘。梁武帝舍身的同泰寺,今天成了少男少女求姻缘的地方,且换了一个名字,叫鸡鸣寺。以及王献之与渡船女的桃叶渡。
这些当然也是如月在水,看到的,仅是一种半梦半醒间的幻影。
北方沦陷,晋室衣冠南渡,江南的烟水气,逐渐消磨了北方汉子的意志,沉湎在这山光水色的温柔乡里,再也不想挥师北伐。
虽说如此,我对南朝一直很迷恋,也始终说不好到底迷恋的是什么,是竹林七贤的潇洒不羁?王羲之醉酒之后的落纸烟云?嵇康临刑前,弹奏的那一曲魏晋绝响?好像是,又好像都不是,它更像是春日里,一场大雨之后,满地落花,一片狼藉里有一种怅惘。
南朝并不平静,朝代更迭如流水,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生命朝不保夕。在那样的一种压抑的社会之下,生命反而有了一种极大反抗与思想的解放,最终呈现的,是无比绚烂的魏晋风流。
南朝最吸引我的,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大概还是那些手帖。其实就是写给朋友的信件,甚至不是信件,只是送给朋友一筐橘或者一筐梨,顺便写了一张便条。因为字迹太美,朋友收到后也不舍得扔掉,装裱起来,成了书法史上范本,后世写的跋文也越来越多,成了长长的手卷,也成了后世历代文人对南朝的集体追忆。
中国书法进入魏晋,大放异彩,北碑南帖。北碑是山水和人文的亲密对话,南帖是一个文人内心的自我独白。当然,也有对恋人的眷惘,对朋友的关念,对先祖坟茔被人破坏,而无可奈何的愤怒。这些手帖,我最爱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最简短的话语,最平淡里的一往深情。
《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送梨帖》:“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
我偶尔也会买点水果送给朋友,却写不了这样的句子。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法集翻到这两张,久久看着,看到那一辈古人的古道热肠。现在的印刷技术好,但也可惜未能得瞻真迹。转念一想,真迹展出,一定人潮如海,到没有此时独处相对的心境了。
《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那是王谢家族南渡之后,某一个大雪之后的初晴,王羲之想起远方的朋友,写下的信件。台静农先生看了之后说:“就这么两行,也不见得怎么好”。确实,它并不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但《快雪时晴帖》的美,不止是在书法,也在文字。短短28个字,是山阴道上的28声轻快的脚步,在历史的纵谷里长时间地回响。
在那个乱世之下,能够送给朋友或者收到朋友的礼物和书信,大概是一种温暖和幸运。因为彼此今天见到,明天未必就还能见到了。杜少陵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读来明明是一纸老泪,点点在墨迹里漫漶开来。
因此“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读来总让人觉得不忍和惆怅,其实,只是想握一握对方的手啊,但也未必能够实现。《执手帖》是王羲之写给不知是朋友还是恋人的信件,只有20个字,真真是纸短情长。
“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
数百年后北宋的某个秋天,柳永与恋人分别,写下千古名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王羲之不得执手,叹此恨何深。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是两种相思,一种闲愁。
长空万古,风月一朝。但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读佛经,开篇常常是“一时”两个字,“一时”用的极好。一时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此类共感,可以跨越时间,远迈空间。
王羲之最有名的书法《兰亭集序》,当然是好书法,更是好文章。那是永和九年的暮春三月,王羲之与友人在绍兴西南的兰渚山下的雅集,时四十二人,赏春修契,饮酒作诗。汇成集子,请王羲之作序。
那是上天握着他的手,写下魏晋最美的风流。
此卷书法读过不知多少次,但也总觉得“惠风和畅,天朗气清”,不只是在讲风景,更是在讲一种心事?这样的日子,在人生里大概是很短的存在,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从六朝博物馆出来,天已大暗,南朝梦醒。在文创买了两只白瓷小鹅,头顶一点猩红,尤为醒目。像是雪里化开的点点胭脂,也像南朝大雪之后,王羲之书房窗外的那一抹红日。
第一次游绍兴,便去了兰亭,刚进门,一池深碧里就有几只白鹅,动静之间,姿态极美,像是书圣笔下的“之”字幻化的。当时在兰亭,也买了四只白瓷鹅,一想,这不也是山阴道上笼鹅归吗?
几天后去到中原,送给朋友两只。剩下的两只,放在自己案头,做笔搁极为合适。朋友后来跟我说,这是从永和九年游来的。我哈哈一笑,果真如此!
王谢子弟,随晋室南渡,是从北方到了南方。我从山阴携此鹅,从南方去到北方。会是另一种因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