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19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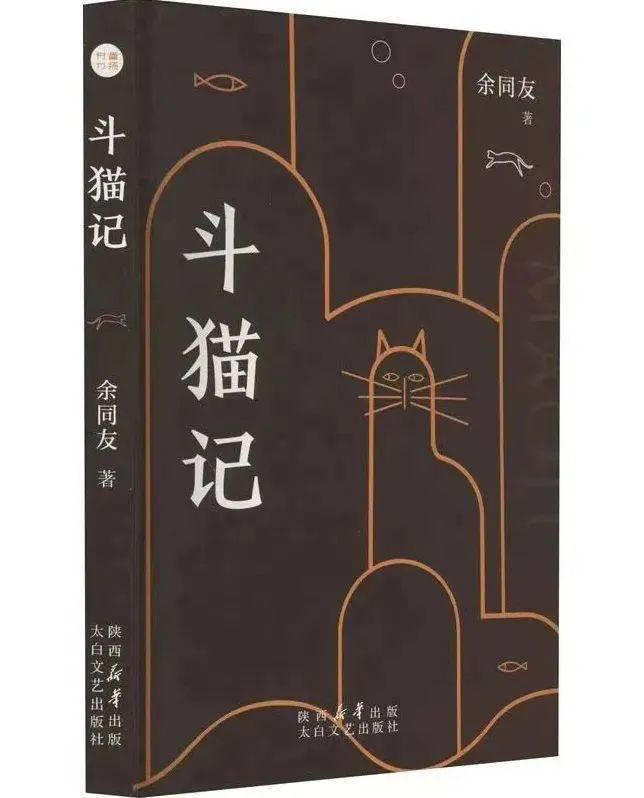
余同友至今已有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发表,可是这位勤奋且又多产的作家,在2018年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去往古代的父亲》。此后的五年间,他又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学期刊上;除此之外,他还有2部长篇儿童小说、4部长篇报告文学出版;这本刚刚付梓的《斗猫记》,则是他第二部短篇小说集。
五年前,我对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进行过研读,并写下了评论。五年后的今天,当我打开《斗猫记》,再次阅读所收录的14篇小说短篇时,觉察到余同友对乡村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现实状况,较之以前有了更为迫切的关注。这种“迫切”对于余同友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它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下乡村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那个“迫切”;二是小说写作者余同友感受到了这种“迫切”,并为这种“迫切”所压。
为了减轻或卸下这种重压,自皖南乡村步入城市生活的余同友,几年来一次次走进皖南与皖西南的许多村庄,“沿着淮河干流走了四省六十多个县”,目睹了“淮河两岸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村庄”(余同友:《短篇小说是第一声鸟鸣——<幸福五幕>创作谈》,《红豆》2019年第7期)中多元且又复杂的变化后,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写作有所创意的他,有了不同于过去的想法。
“想法”是一个名词,很抽象,当“想法”遵从作家意愿,成为“想办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动词了。在今天,我们谁又能生活在现实之外?我们的作家即使看一看自己所在的社区居民常驻人口构成情况(在很多城市社区,本地户籍居民常驻人口数量已明显小于外来人口)的变动,听一听街市上异于这个城市本籍居民南腔北调的口音,也能感受到城乡这两种人口变量,而带来的文化、生态、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变化。更何况,随着城镇化推进,原本聚族而居,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乡村社会,其“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人际结构不断的变迁”,实际上导致了“熟人社会向‘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的演变”(陈文胜:《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这样的“变迁”或“演变”,在乡村城镇化未进入成熟期之前是巨大的,中国千百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拨动着不甘于平庸的作家的心弦,使优秀作家难以置身正在衍变的现实之外,不再满足以往积累的乡土文学写作经验,依据所处的社会背景,在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或各有所创新。
读余同友的短篇小说近作,我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位没有将当下的乡村与城市分割开来的写作者。在他的叙事视域中,无论是皖南山里的“瓦庄”“屏风里”“画坑村”,还是淮河岸边像“黄台子”那样的村庄,总是与城市(镇)或紧或疏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相互交织的程度,因小说中必定会出现的那个人物的身份、经历、情感不同而各有所不同。余同友就像是站在城乡尚未弥合地带的那道狭长的缝隙中,其小说的架构、叙事的秩序、情节的伸延,细细品味,大都是在一个或几个城里人的推进下展开的。如果将这些属于“城里人”的人物抽离,其小说所建构的图景将不再结实与完美。
在余同友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幸福五幕》里的王文兵,早已走出村庄、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与他的前妻都是大学的副教授;《丢失的瓦庄》里的“我”和“我”的父亲,如今一家人都生活在离家乡一千公里之外的罗城,多年才回一次瓦庄,也仅是为了给奶奶做八十大寿;而《树上的男孩》里的张克军、陈玲玲这对夫妇,一个是罗城大学某学院带博士生的研究员、一个则是有望进入大型国企中层的白领;即便《铜钱铁剑》里的那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城市打工者阮和刚,四年才回一次淮河边的村庄,也只是为了儿子想在城里买的那套商品房要五十万,可是还差十万,因而他觊觎着仍在乡下打铁的父亲压在熔炉砖块下的——那枚据说价值十万的“乾隆通宝”铜钱。
凄美的《牧牛图》更是如此。这篇小说以隐晦的笔墨,多次暗示读者那位从城里来到“画坑村”摄影的女人,因为太像四十年前的插队知青——画坑村小学代课老师小张,即便胡家兄弟俩希望是她,但最终也未能确定她是不是当年的小张老师。
作为小说要素之一的这些“人物”,即便最初的身份是农民,或曾经在农村生活过,但在今天,他们已与“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1年11月29日第14版),他们都在距离乡村或远或近的城市(镇)中生活与工作,事实上是在城市上班或务工的城里人。
现代文学认为,文学终归是“人的文学”。余同友将这些人的“城市”感知,代入他所叙事的“乡村”社会,既是他多篇小说叙述策略的需要,也是他对当下乡村城市(镇)化新的文学理解。他想要写下的,不再是以往小说家叙事中出现的那个“乡土中国”,而是“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这一巨大裂变与弥合期间——那极其复杂的乡土社会现实,并从这些“人物”的个性出发,艺术地指向这一特定环境中人的命运与人的生存境遇。
怎样结构短篇小说的情节与故事,对于很多小说家来讲,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幸福五幕》中,我看到了余同友的努力。幕开幕落,各五次。其中的人物、场景、事件,随着幕布的拉开又落下,我看到了乡村城镇化过程中有些人的幸福与疼痛。这是余同友以戏剧手法精心设计并演绎的《幸福五幕》。
《幸福五幕》中出场的人物实际上只有三位:八岁的王子涣(小学生),王子涣的父亲王文兵(大学副教授),王文兵的母亲王腊梅(黄台子整村移民建镇后的“幸福花园”小区居民)。韩小兰虽然也曾在“幸福花园”出现过,但那是前年的事情了,今年春节之前已与王文兵“办过离婚手续,独身一人去了澳大利亚”,因而今年回到“幸福花园”陪母亲过年的,只能是王文兵和他的儿子。
《幸福五幕》的故事,是从王子涣好奇地发现奶奶“半夜起来趴在床底下念咒语”开始的,他觉得奶奶太像他读过的《格林童话》中的“巫婆”了。或许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第四幕中才出现的那只黑陶罐。这只黑陶罐并不是一个空罐,在这“五幕”剧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物的在场”,它所灌装的“东西”,既是王子涣深夜醒来时闻到“一股奇怪气味”的所在,也是王腊梅能够暂时缓解耳朵里那挥之不去的鸭子叫声的良药。藏在床底下的“黑陶罐”和那根吸管,犹如经典戏剧中的道具及辅助道具,它被余同友打上了追光灯,吸引着父子二人的目光,对于剧中的人物与观众(读者)就像是一个隐语,在未揭开谜底之前,似乎想请他和你都去猜测一下。
是“迷”的隐语,自然会有人给出“谜底”。揭开“谜底”者是王子涣,是王文兵,也是“迷”的隐语制造者王腊梅。
这位“从三十一岁那年丈夫去世,就接过养鸭的营生,一养就养了三十五年”的母亲,因淮河行洪区需要,整个村庄移民迁住镇上“幸福花园”小区时,曾经有过“没想到老了老了,我还成了城里人,住上楼房了”的喜悦,但这种喜悦不久便消散殆尽,对新的生活环境充满疏离、陌生、孤独感的她,是多么怀念“那些鸭子嘎嘎的叫声”。况且养鸭曾经远近闻名的她,还有医治鸭子“瘫腿”(鸭掌红肿,站不起来,慢慢就挣扎着倒地而死)的秘方。
这“秘方”、或“谜底”,即是“棉籽油”。它是医治鸭子“瘫腿”病的绝招,多少年来,王腊梅从不示人,如今就装在黑陶罐里,那瘫腿的鸭子喂上一点,病就好了;王腊梅如今吸上一小口,“耳朵里的那些鸭子就不叫了”。
这只黑陶罐简直就是一件法器。没有它,这篇小说将缺乏诱惑力,如果早于第四幕出现,这篇小说的故事有可能过于直白,抑或会失去现在的精彩。
这自然只是我这个读者的判断,但我在“黑陶罐”及罐里的“棉籽油的气味”中,感受到了作者的智慧。这智慧不同于我们常常要说的灵感,它藏匿在少数作者心里,当较为平淡的故事需要时,它会被“怎么写”的作家很珍惜的——而且是压轴式地放进小说里。
依我之见,这“幸福”的“五幕”,其实自“第一幕”开始,那先后出场的人物与道具,就接受了余同友的调遣,他们不仅进入了各自的“角色”,而且经过“五幕”中多个场次层层递进地表演,都成功地演绎了自己的形象。余同友将这“五幕”剧中的“幸福”与“不幸福”、甚或难以言喻的痛苦,一幕一幕地推演到我们面前。
《台上》的故事仍然与淮河有关,而且就在淮河岸边,但如何去解构这篇小说,余同友却另辟蹊径。这篇小说开头就有些意思,它摘自《淮河水利手册》对“庄台”那不到一百字的说明。历史资料中的文献,放在将要讲述的故事之前,本身就具有“元小说”因素,它在余同友那里,是不是表明了他所虚构的这篇小说,其故事的真实性最初始源于历史中的这类文献碎片?
《台上》是以29个小时中8个确切的时间节点为引语(类似本篇小说中的小标题),并依照时间的顺序来完成整体叙事的。其叙事轨迹中的场景、情节、人物,都在29个小时(2018年10月13日晚上7点—10月14日夜晚12点)中。但余同友笔下的这段时间,并不止于这封闭的29个小时,它通过老范不断地追述与回忆,获得了多个空间的扩张与延伸,使“过去”里的“事件”及“事情”回到了“现在”,这也就很自然地改变了以时间为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
在这篇小说中,读者或许会注意到,这段时间之外最重大的“事件”是一个村庄的消失:“二十多年前因淮河治理需要,滩地十年九淹的黄台子,成为第一批行洪区”,整村迁到了“十几里外的镇上”;不愿离开黄台子的老范夫妇,也因此成为留在村庄遗址上的最后两个人。而此重大“事件”,在老范眼里,则是二十年后的今天,“与老范未出五服的堂兄弟”——范六三小儿子范团结,因犯命案躲藏到他童年生活过的这个村庄,于14日夜晚,被追踪而至的刑警枪击伤至腿骨,而擒获归案。
《台上》的故事看上去虽是简单,但余同友却以枝蔓横生的笔墨,赋予它难以言尽的意味。我们看到,作家是借老范所看所闻、所想所思,叙述黄台子的前世今生、兴盛和衰落。其中,迁建前“一百四十多口人”挤在黄台子“大晒场”上看露天电影的热闹场面;老范家不知去向的大黑(狗)与在“别人家老墙上像干部那般散步”的大黄(猫),“叽叽咕咕拥挤着钻进鸡栅里的鸡公鸡婆”,林子里默然无声地站在树梢上的乌鸦,傍晚时分鸣声响亮飞进窝中的鸟雀……等等情景,都在余同友的笔下进行了细微的描述。这种描述无疑是写实的、具象性的,它能够“立意于象”地使老范这个人物形象丰满地站立起来。
然而余同友似乎并不满意仅仅这样的描述,我惊诧地读到:他借助无形无状虚幻的“风”,来思考人的许多感觉:老范与范六三,因两家之间的地沟开挖位置发生过争吵,“二十年没说过话”,但老范目光仍然会投向他家早无人间烟火的房子。范六三家的门锁锈蚀脱落、被风吹开,老范可以“找根铁丝把门环穿上把门重新掩上”,但他从没进去看看。因为那刮了“几百上千年的风”能够代替他走遍范六三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而且走在每个角落的“风”声是不一样的。房屋本是人类容身之地,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但没有人住的房子,只能任由“风”进出。这无形无状的“风”,自这篇小说的第三章(即“2018年10月14日凌晨3点”)开始,竟断断续续地刮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其用意显然是借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来描摹老范的心理活动,使“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重叠在这29个小时里。
《丢失的瓦庄》《树上的男孩》《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以及《斗猫记》等短篇小说,则凸现了余同友感知和表叙这个世界的另外写法。在《丢失的瓦庄》中,那个“我”,是个虚拟的人物,是余同友借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行为的承担者,他既是寻找瓦庄这一“事件”的叙说者,也是参与者。
令人诡异的是,当“我”从遥远的罗城乘列车到县城,再坐中巴车到镇上后,竟发现自己来到全然陌生的“前江工业园”,找不到五里之外去老家的路了。可是上中巴车时,“我”看到车前玻璃上的行车线路明明是“县城—瓦庄”,但那位售票员和司机却告诉他,“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叫什么瓦庄的地方”。天色将近傍晚,身负父亲之命去瓦庄给奶奶做八十大寿的“我”,想在地图册上找到瓦庄,可是地图上的“瓦庄”却变成了“前江工业园”;更为蹊跷的是自己身份证上的“瓦庄”、手机百度上的“瓦庄”,均已消失不见。即使“瓦庄”确实存在于“我”的回忆中,它此刻已不见踪影。陷入噩梦中的“我”,只能求救于“前江工业园派出所”民警,但民警却认为疯颠的“我”可能受到了什么刺激,硬要编造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将“我”约束到翌日天亮,才敢放“我”离开。
故事至此尚未结束。潜隐于叙说者背后的作者余同友,将“我”再次扔进瓦庄“存在”与“不存在”的悖论中:返回罗城的“我”,在回到家中的那一刻,地图册、手机百度、身份证上的“瓦庄”竟变了回来;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镇上,原本那个打不通的村长老徐电话一拨就通,接过村长电话的奶奶埋怨孙子道:撒个谎都不会,让她伤心地“等了一天一夜”。没有人相信“我”的遭遇,即使“我”的女友李娟也不相信。为了证实儿子所说的遭遇是谎言,父亲请完假,竟立即乘动车去了瓦庄。
然而几天后才返回罗城的父亲,与“我”经历的遭遇别无两样,故乡的瓦庄,也被父亲弄丢了。而奶奶的电话里的“你骗我,你父亲也骗我,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那句话,虽然在父亲那里佐证了“我”的遭遇并非是谎言,却让伤心的奶奶深陷在儿孙双重“谎言”的痛苦中。
瓦庄的“存在”与“不存在”,是余同友给叙说者“我”设下的一个叙事陷阱。这个叙事陷阱将“我”逼进了一个近乎梦魇的境地:只要你离开城市,去寻找故乡时,地名的“瓦庄”便会消失;只要你离开乡镇,返回“罗城”家中,“瓦庄”这个地名便又会莫名其妙地浮现在眼前。读这篇小说,或许我们应该察觉到,“我”所叙说的故事虽是荒诞不经,但又隐伏着现实中的真实,那即是:对于走出乡村、已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的那些人,今日村庄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在日渐衰退,村庄的“丢失”将是他们难以避免的结局。
与《丢失的瓦庄》比较,《树上的男孩》和《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也颇具荒诞性。但前者的荒诞,显然是在叙说者“我”的地理坐标转场(从城市到乡镇,再从乡镇到城市)过程中才实现的,而后者的荒诞虽然也与叙事空间转换有关,但并非是直接的因素。
直接的因素是张克军、陈玲玲这对夫妇的孩子管管,和“我”的女友父亲老吴都是病人:一个患有自闭症,必须在腊月二十八就动身赶往乡村的屏风里,找到四天前请假回家过年的保姆兰姨;因为这些年,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唯独这位兰姨孩子能接受,几年下来,管管已离不开兰姨了,更何况七年前热恋中的张克军和陈玲玲以身相许时,便在屏风里认识了这位兰姨。
另一个则是患有恶性脑瘤,住进肿瘤医院后,觉得生命时日不多,想让准女婿的“我”满足他这一生中最后的酒瘾;可是喝过酒后的老吴便有了醉意,先后竟将“我”当成了自己的两位教师朋友张大桥与许卫国,在回光返照中追溯了自己青年时期与瓦房村姑娘王芳的缠绵情事;更为离奇的是,或许是那一杯酒再次发生了作用,老吴颠三倒四地又将“我”当成了警察,说出1986年县中学纵火案的秘密:那个烧死王芳的人就是他自己。
没有人愿意自己将来的岳父是纵火杀人犯,作为准女婿的“我”,听到老吴这番话,不仅担惊害怕,且有了恐惧。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心理障碍,迫使他下意识地充当了“求证”者,找到了与老吴同届大学毕业,分配到县中学的许卫国,以期获得事实真相。
荒谬随之而至。当“求证”面对的不是数学几何证明题,而是与自己有着利害关系的“案件”时,这个“求证”者的“我”,竟又让自己成为了“破案”者。即使这样的“破案”并非合乎法理。作为读者,我在这错综回环的故事中,再次看到了余同友娴熟的小说叙事技巧:在多条线交织的叙事中,对人物视角运用的重视及别出心裁,这个“我”,在小说作者那里,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但与《丢失的瓦庄》中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我”有名有姓叫小章,在读者面前,他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是自己的经历,均源自老吴、许卫国的回忆,以及“我”的未婚妻吴小越对父亲的印象。
也正是老吴曾经最要好的朋友许卫国回忆性的讲述,让1986年县中学纵火案水落石出:老吴既不是纵火者,更不是什么杀人犯,“烧死王芳”只是老吴病重回光返照时一个荒谬至极的臆想;王芳也没死在那场大火中,前些年还回来参加过许卫国组织的同学会活动,当年她是因为老吴胆小懦弱,屈服于缠上自己的那个小混混的持刀威胁,而没有遵守她与他的约定——辞职与她私奔,她只能一个人伤心欲绝地去了东北,另嫁他人。
因此,这以第一人称“我”——“小章”所讲述的故事,只是对老吴、许卫国等人所叙之事的复述。如果从小说叙述视角去分析,如此的复述,虽经“我”说出,在本质上仍是“他说”。
但此在的“他说”,因为使用了第一人称,仍然不是全知视角的无所不知,其所知道的依然是有限的,或然性地露掉了某个环节、某个真相,那是余同友留给读者的判断选择。比如,县中学的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至今仍未明了,交由读者判断。
而《树上的男孩》的叙事方式显然没有这么错综回环。患有自闭症的小男孩管管,由于保姆兰姨离开罗城去了老家屏风里,其病症表现愈加明显,他自兰姨离开的那一天起,面无表情,也无言语,整天盯着墙壁上张克军七年前拍摄的那幅《屏风里的春天》,四天没吃一口东西。因此,无可奈何的张克军决定带上妻子和儿子,立即动身,要把兰姨追回来。这便是这个故事的开端。
可故事的结尾不仅魔幻,而且让我有了和张克军、陈玲玲同样的惊愕:到屏风里,管管没有见到他们一家人要找的兰姨,却一眼看到了《屏风里的春天》中的那棵枫杨树。
这棵树在这个时候出现,具有独特意义,它不再是风景照片上的树,而是现实风景中的枫杨树,正是这棵树由于从二维平面转到了三维立体空间,一下子便戳中了这个小男孩的心,所以才有了他“一扫平日行动迟缓的模样,跑到溪边的大树下,两脚一纵一纵,那么高的大树,他竟然一会儿就爬到了树端”,坐在树杈上的管管神情忧郁,像“猴一样反手搭着额头,目光望向远方”,犹如一个哲学家在思考什么。
其实,除了这个故事的开端与结尾,小说中的人物张克军、陈玲玲、小男孩管管,以及与这三个人物有所交集的物事,都在那辆小车上——那辆车行驶在罗城到瓦县屏风里的路上。兰姨虽是这篇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但她并没有在这个故事中直接出现。张克军与她的三次相遇:前两次是在屏风里兰姨家中,后一次是为请一个好保姆,在家政公司遇到兰姨,请回家后,没想到管管不仅接受了她,而且对她依赖的程度超过了他和陈玲玲……这些情景及情节里的细节,都是驾车的张克军断断续续的回忆所提供的。
由此而来,这1100公里的路途中张克军的“回忆”,可以被我视作是这个故事开端与结局之间的前铺后垫。这“铺垫”自这一家人坐进车子后,它的两头便连接着故事的开端与结局,也连接着吃遍了“各种新药、特效药仍不见好”的管管非得去屏风里寻找兰姨的动因与结果。
结果,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那个答案。因此张克军听到了树下陈玲玲那一声颤栗的尖叫,“危险,管管,你下来!”可是小男孩从那棵树上下来后,陈玲玲又如何去面对?难道她应该谴责七年前的春天——她和张克军在屏风里热恋时的那次激情,而孕育了她和张克军的孩子?
《树上的男孩》看上去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如果贴近人物与场景仔细观察,虽然故事中出现好几个人物,但所叙述的焦点始终落在张克军身上,读者是能感到以第三人称所叙说的人、物、事,均是张克军的视角。我之所以再提叙述视角,是因为在这篇小说中,除张克军外,没有别人可以充当故事的叙说角色,如果换了别人,那将是另一篇小说。这其实是“一种内在式焦点叙述,这种第三人称实际上已接近于第一人称叙述了”(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220页)。在我看来,这样去叙述,可以促进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信任——可靠的叙述者与可靠的读者。
《斗猫记》实际上也采用了这样的叙述角度,其焦点是落在朱为本身上的,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变形。我们看到:闯入朱为本视野的,首先是那只猫,一只怀孕的白猫。会做冻米糖的朱为本,算是瓦庄的一个能人,当他心事重重走进自家院子,瞧见这只“肚皮快拖到地上的”白猫时,故事中所有的人物:老伴王翠花、孙子朱小森、卖泥鳅的王德胜、镇上糕点店的老板以及准备回家过年的儿子儿媳,先后都与他及他憎恶的那只“模样怪异”的猫,发生了纵横交错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人与猫的这场战争中,那只怀孕的白猫,由于老伴和孙子的善待,面对朱为本的喝斥、脚踹、吹火筒赶、竹竿捅、弹弓打,总有办法与他从容地周旋,就是赖他家里不走,这便成了朱为本的噩梦。
可是朱为本又不能将他憎恨这只猫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这是一个必须窝在朱为本心里的秘密。这个秘密自朱为本从市医疗机构拿到后,便藏在他的口袋里,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因为他无法面对村里人的议论“这孩子像他妈”的言外之意。那张纸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敢将纸上的内容告诉在外打工的儿子,更不敢告诉去年因高血压轻微中风过的老伴王翠花。有意味的是,作者余同友在这篇小说即将进入尾声时,才借朱为本的视角,道出这张纸的秘密即是“亲子关系鉴定报告”。试问之,在瓦庄、或瓦庄这样的乡村,有谁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孙子,不是血亲意义上的亲儿子、亲孙子?如果老伴与儿子知道了这张纸的存在,朱为本这个家的“天就塌下来”了。这张“亲子关系鉴定报告书”,是小说家余同友对笔下的情节、背景、人物(也包括那只猫)的设定,它既是人与猫之间战争的根源,也是导火索,朱为本正因为这张纸的存在,才让他觉得儿媳“丁秀丽的脸长得和那只来历不明的猫特别像”,从而导致了他那不可理喻的怪诞行为。也许我们能从这张很轻又很沉重的纸上,看到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的现象还在今日城乡弥合期间的社会上演,朱为本和他一家人的遭遇,也仅仅是这个时期的一点投影而已。
我们还是来看看小说是怎么结尾的吧:值得庆幸的是,噩梦中醒来的朱为本,将拌进“毒鼠强”的“那盘香喷喷的干泥鳅”扔进了灶膛里,因为他刚刚梦见老伴和朱小森因误食干泥鳅,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其时,王翠花已领着朱小森来到院门前,那“爷爷!爷爷!”欢快的叫声,让他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应对。而屋顶上的那只盘腿而坐的白猫,此刻已经不见踪影。那只猫好像比朱为本更诡谲、更聪明,是它终止了这场战争,让焦虑的朱为本再无事可做,只能像那只猫一样,喉咙里发出“喵呜——喵呜——”的叫声。
可是,我们从朱为本这猫一样的叫声里,并没感到他和他们这样的“战争”,就此能结束。
这也是此篇小说作者余同友给我们的提醒及示意。
在余同友的短篇小说中,《牧牛图》有可能是一个特例。这些年,我陆陆续续读过他的五十多个短篇,却从没读到他以如此静寂的方式去叙说一场雪。
这场大雪,仿佛给余同友打开了一个新的写作空间,我看见,他所架构的这个小说文本图式,由于是建立在风景如画的“画坑村”地基上,便不再像他多个短篇中所显现的那样——在结构上波诡云谲般的复杂,在叙事中所漫溢出的荒诞及语言的诙谐,其叙事走向及故事中的情节,清晰得犹如被画坑村山里的大雪照亮。
《牧牛图》如泣如诉所叙说的故事是疼痛的,主要人物胡芋藤的性格形成及他兄弟俩的结局虽是凄凉至极,但在余同友那干湿浓淡相宜相辅的笔触中,仍让我读到了中国画笔墨里所带来的那种美学意境,即便那是一种冷抒情背后的凄清凛冽之美。
我在《牧牛图》中看到:当那个女人“抱着一架黑色炮筒样的照相机”,走到胡芋藤、胡芋苗身边时,哥哥胡芋藤就觉得她像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在村小学代课的老师小张。四十年过去了,胡芋藤的记忆依然清亮:他20岁那年给小张挑完水,路过教室时见小张老师不在,放下水桶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了“张老师您好”五个字,后来有人告诉他,小张老师说“这字写得不错”。也正是小张老师的夸奖,让只“念了三年书”便辍学务农的胡芋藤,对模样好看、说话京腔京调好听的这位姑娘生出爱慕之情。然而这只是他单方面的情丝,除了“字写得不错”那句话外,他即使再努力,也没引起小张老师的注意,更别说得到小张老师的青睐或亲近。
在胡芋苗眼里,能让哥哥与小张老师彼此体肤贴近的,是那个“下雨天,山洪暴发,公路冲断”,让站在河边立即想“赶回城去看生病母亲”的小张老师急得哭了起来。胡芋苗赶来时,见哥哥背起小张老师已摸索在湍急的河水中,直到“洪水退过后的第三天,累瘫的他才回到家中。”自此,“哥哥的腿出了问题”,几个月后一条腿坏死被锯掉,剩下的那一条好腿,也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开始跟他过不去”,常常痛得他欲死不能,只能痛苦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哥哥即使知道小张老师那次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到画坑村的真实原因,其实是“急着去县里办回城手续”,也从没怨恨过她。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与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这场大雪是余同友给这个短篇定下的一个基调,它流露了作者书写此篇小说时的思想感情与写作态度,如果不围绕这场大雪,小说叙事的构成将流于结构的表层,因为那也是胡芋藤、胡芋苗兄弟俩所盼望的大雪。在《牧牛图》中我们见到:来到画坑村摄影的那个女人,答应过兄弟俩,“这里的景色我拍得差不多了,下次我就冬天来,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一定来,我估计冬季的雪景应该是不错的。”显而易见,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知晓:等待“冬季雪景”来临,再次面对相机镜头表演的兄弟俩,实际上是在等待那个像小张老师的女人到来。那张出自这个女人之手,获“国际大奖”的摄影作品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它就放在兄弟俩房间里,“面朝着胡芋藤的床,看到这幅相片,胡芋藤那难以忍受的腿痛就好像减轻了一些”。
那张装进像框的大照片无疑是美丽的:因为在“轻烟漠漠、白鹭斜飞、老牛慢走、垂杨吐绿”的水田景色映衬下,兄弟俩曾按照那个女人的要求,“穿蓑衣戴斗笠”,弟弟犁田、哥哥放牛,细雨打在他俩那“暗含喜悦”之情的脸上,宛如一幅水墨勾染的“春耕牧牛图”。
但这种喜悦只保留在相片上。为了等待在“冬季雪景”中的表演,兄弟俩在冬天到来之后,雪还没落下来的时候,便穿戴好蓑衣与斗笠,赶着牛拉着犁,在画坑村的土地上进行着表演之前的预演。那场大雪终于落下来,而且是“一连下了三天”,兄弟俩也在雪地里演了三天,仍然没有等到那个想拍摄“雪中牧牛图”的女人到来。
这第三天的夜晚,将兆示这个悲剧的结果:筋疲力尽的兄弟俩晚饭也没做,都倒在了床上。天将黎明时分,当胡芋苗听到因疼痛而咬着筷子的哥哥在喊着他的名字,要他“帮帮我!帮帮我!”的时候,梦中惊醒的弟弟,看见哥哥竟然和那个面色凶恶的女人厮打起来,他“拿起一个枕头往那个女人脸上闷去”,直到那个女人再无动静。放下枕头的胡芋苗,这时才有点清醒,觉得不对劲,拉亮电灯,并不见那个女人,那个被他闷在枕头下是哥哥,已在自己的眼前死去。
在我看来,这个女人是不是当年的小张老师,似乎小说作者也不愿意说破,余同友好像是有意识地不给读者标准答案。我们只能从四十年前后——小张老师和那个女人同样夸奖胡芋藤“字写得不错”这句话,以及“那个女人的脸”在兄弟俩眼里“还真有几分像”小张老师,去猜测那个女人有可能是小张老师。然而这“可能”中又有着“不可能”,因为胡芋藤曾问过那个女人是不是姓张、是不是当过老师的时候,那个女人诧异地回答道,“是啊,我就是姓张,你们怎么知道我姓张呢?不过”。她说完“不过”这两个字之后,便无下文。从这个句子的语法来分析,连词“不过”是对前面那个句子的转折,后半句话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认为在肯定自己是姓张之后,却又是对“当过老师”的否定,只是她觉得没有必要向一个被拍摄对象说出后面的话而已。
如果认真审视,当下的短篇小说写作是处于边缘地带的。许多小说家放下了他们曾经热爱的短篇小说创作,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自然是传媒与批评界市场运作的结果。
在此环境下,哪位作家还能一如既往热爱他的短篇小说,尤显珍贵。这也是我多年来持续注目余同友短篇小说创作的缘由。这回再次评论他的短篇小说近作,是我继五年前对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进行评论之后的再次文学追踪,它表明了我心之所想:期待有更多人去阅读他的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杨四海,中国作协会员,在《散文》《散文选刊·选刊版》《长江文艺》《文艺报》等发表作品;出版有散文集《河边叙述者》等三种。作品被收入《21世纪中国最佳散文(2000-2011)》《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1》《新散文百人百篇》《零距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等多种选本;散文集《河边叙述者》获湖北省第九届文艺楚天奖文学作品类特等奖;多篇散文曾分别获得湖北省文艺楚天奖文学奖、《安徽文学》年度散文奖、长江文联文学创作成就奖等。
转自:安庆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