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11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近期,我省作家陈家萍短篇小说《独角牛》发表于《莽原》2024年第1期;短篇小说《白天鹅之伤》发表于《当代小说》202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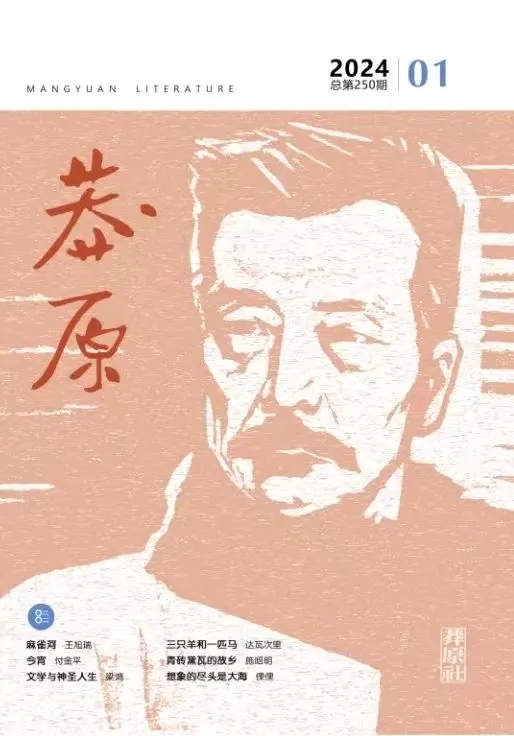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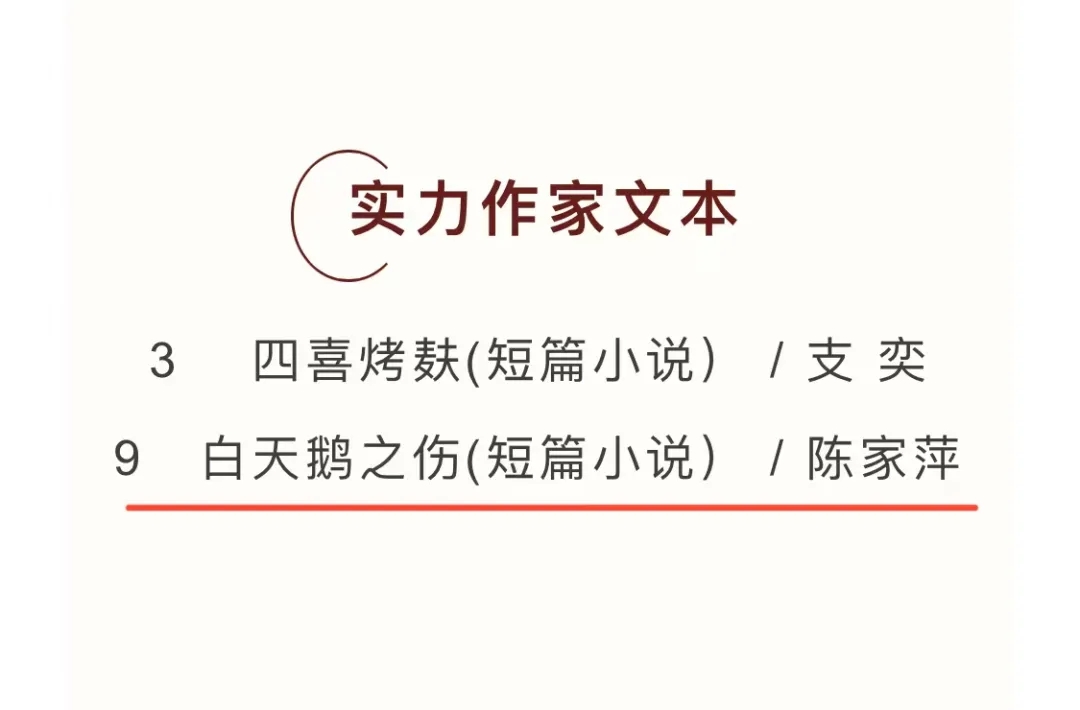
作品欣赏
独角牛(节选)
陈家萍
尕老汉是被窗外的月光烫醒的,睁开眼,一片软刀正砍向胳膊,放出黄灿灿的光,他伸手握了握,握一手酥软,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皮肤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透骨的冰凉和尖锐的滚烫。哪里传来的酒歌?他屏息凝听,混入夜色和雾气中的苍茫歌声伸出一只手,牵引他下了床,“嘎吱”一声抽开门闩,踩乱一地树影。
遇迎头风,走两步,退一步,酒歌趔趔趄趄,这才惊觉,酒歌不在别处,发自他的腹腔。啊,我又能唱酒歌了!尕老汉仰天长啸,声震林樾,“酒—酒—歌—歌”,风愈狂,歌愈烈,山谷回音,余音不绝。
尕娃时代的他受高人指点,学会用腹腔唱酒歌,这绝活让他出尽风头:在首席坐定,眼风一罩,四围安静,他从腹腔吟出的酒歌,一搓一揉一推一搡将酒意缭绕至酣畅,把宴席的氛围推向高潮。突然一天,腹腔哑了,他再也吟唱不出酒歌了,这是哪天的事?
被风卷到山顶,月华兜头浇下,淋湿冈头一只拜月的黄鼠狼。以前听老人讲古,什么月圆夜黄大仙集体拜月,以为那是胡编,今儿个真就见了!尕老汉不错眼珠地瞅,这黄大仙显见得也老了,动作迟缓,姿势僵硬,拜完月,它扭头瞅了眼尕老汉,点点头,倒把尕老汉惊出一身冷汗。它笑眯眯地走了,走的方向正是菩提村;月光下的村子也老了,被黄鼠狼一步一步给走老的。
尕老汉眼前出现两条歪斜山道,它们像两排犬牙,把这座凤凰山一咬两半:东边为生道,山下住着数户人家;右边为魂道,乱坟岗上栖息着无数往生的灵魂。脚自动朝向乱坟岗。也不知怎么就坐上高高的坟丘,手一摸,摸到一瓶酒,喝一口酒,对着月光唱一段酒歌,那模样像极一匹孤独的老狼。
金杯银盏斟满酒,大姐端来米粉肉,爷儿们,甩开膀子喝个够,喝够酒没烦忧,春天过完到夏天夏天过完又是秋,吃块米粉肉润润喉,米酒喝了不上头,做人也像酒醇厚。
尕老汉唱酒歌不需要脚本,可以望风采柳,他唱天上那盏圆灯笼,月光像乱箭般在密林里“噗噗”蹿来蹿去,有几支射到他身上,把他射清醒了,认出坐的是老伴的坟。他颤着手摩挲着坟土,摸到一块土疙瘩,捏成碎末,均匀地撒在坟上。捏完一块又捏另一块,他捏得如此细致,神情肃穆、姿态虔敬,似乎碾碎的不是土疙瘩,而是艰难岁月中的磕磕绊绊、世事纷扰。他碎碎念:这坟土呀,就是她的衾被哩,万一硌着她可如何是好?
他那永生的泥屋新娘哟,可爱美了,一头青乌乌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褶子捋不齐整就不出闺门。
“你傻啊,我比你大。”
新婚之夜,速速打发了一帮酒鬼,他早早到洞房,挑开红盖头,她头一抬,眸光一闪,晃得他失神。
不,他心里话,我才不傻:“我太奶奶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娶要娶世上的好女子。’”
“你傻啊,娶了个空壳。”
他抓住她的手,放到自己的心窝——她的手冰冰凉,烫得他一哆嗦,望着她的眼睛,他一字一顿:“不怕,我——”他想说,这颗心是滚烫的,掏给你,随便用。这些话不知怎么打了结,绊住了嗓眼。
“你傻啊,”丹凤眼里浮上了雾,“为啥把我从棠梨树解下,我本……”
他捂住她的嘴,沉声道:“我太奶奶说,除死无大事。”
“好个除死无大事,”这句话就像火柴噌地擦燃了那双著名的丹凤眼,他被那瞬间迸发的璀璨惊住了。她的美,照亮了泥屋。连屋外听房的人也噤声。她咬破手指,把血挤到掌心,抹上嘴,唇红齿白;抹上脸,粉面桃腮,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好,好。有你,有这些话,足够我活上十年。我给你生儿子。”
地上晃来一只牛角。他揉了揉眼,没错,独角牛。他摸着独角,“果然是你。二十多年未见,你我都老了。”独角蹭着他,把泛黄岁月中的熟悉感觉给蹭出来了,这熟悉感觉在全身到处跑,荡到心里,心发痒;蹿到鼻孔,鼻子发酸;钻到眼里,眼睛发胀。他哭了又笑:“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见我啊。”
它曾有一对威风凛凛的双角。
它曾是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犁田好把式,力气大得邪乎,有他的酒歌助兴,拖着犁驮着耙,行走如飞,再大的田也不够它耕。卷几舌青草,它就恢复了力气,追着母牛跑,四处找伙伴打架,两只角像铁铸的弯刀,发出凛冽寒光,牛们打眼瞅见它掉头就逃,它还不依不挠,他只好返住角好生相劝:“穷寇莫追。”
独角牛和尕老汉都曾拥有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婚房是五间茅草房,堪称当时的豪宅。松毛扎大脊,土坯取自他分得的地,泥墙、泥地都用白泥一遍遍刷得平滑光亮——白泥是本地特产,可当水泥用。
泥堂轩敞豁亮,她是永生的泥屋新娘。
动物亲昵泥屋。堂前燕子呢喃语,檐下麻雀叫喳喳,清早喜鹊来报喜,撒欢的还有猫狗、鸡鸭与墙头的喇叭花。墙上无数洞眼,那是蜜蜂的家。——它们飞进开成一片金的油菜花地,飞进桃花丛,连满院阳光都嗡嗡有声。
婚后第二天,她把自制烟丝倒在纸上,卷好,到灶火上点着,递给他:“太奶奶说,不能断了烟火。”
他懵懂接过,糊里糊涂去抽,半年后顿悟:指间一缕闪烁的微光,一日三餐的炊烟,她微微隆起的腹部,绞的剪纸,氤氲在他腹腔的酒歌,共同构成这五间泥屋不灭的“烟火”。
黄爪搭在巢穴,雏燕探头,睁着小黑豆似的眼睛瞅啥?一束太阳光柱从门外射入,罩住了她,给她镶上金丝银线,镀上金粉,她端坐竹椅上,脸上毛茸茸的细绒毛清晰可见。她穿着鹅黄色细开司米毛线夹,脖上系着柳绿色丝巾,只见剪刀在白纸上旋转翻飞,白菜和小兔子、和平鸽和牡丹花很快就剪好了。她在和摇窝里的小婴儿说话哩:“用锯齿纹,白菜、牡丹花的花脉、叶脉,猫毛、鸽子、马的鬃毛,动植物就有了质感。”她把剪纸抖开:“瞧,鸽子边上还有铜钱纹呢,在民俗当中,鸽子是吉祥物,牡丹花开富贵。”
可不,她一刀刀剪出来的都是对人世的好意。
“还有月牙纹、云朵纹、火焰纹……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啊。”
胖小子咿咿呀呀,小东西能懂个啥?荷锄而归的他笑了。
他倚门而立,看着她,这永生的泥屋新娘,她把周围的世界照亮。一株巨伞样的杏树抱持着东厢房,雨丝一撩,杏花就开淡了,红红白白;西厢房一墙牛屎巴巴,阳光一晒,一股子松爽干甜的青草味儿,惹得蜻蜓满场飞。她专挑白净的,捏碎了,放瓷罐当粉用。这粉混合了婴儿的汗味、奶腥味,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儿,他一直没能辨别出来。不像姜,不像蒜,不像花果,不像任何庄稼,回忆到这儿,他猛地抽了下鼻子,深呼吸,从时光深处扑过来的一股清香撞得心口疼,他恍然大悟:那是幸福的味道啊!
那时,门前,凤凰山上白鹭飞,雨后草丛中冒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松菇,那是凤凰山神的恩赐,油公鸡炒松菇,咬一口,妈呀,鲜死人!
那时,屋后凤河,一网下去,就能熬一锅虾糊。船上立着鸬鹚,一个猛子扎下,捉了红尾,再捉鲫鱼。苍茫的渔歌响起,泥屋炊烟即起,袅蓝了菩提村的天空。
那耕牛遍地走的村庄,到处弥漫着蜂飞蝶绕的幸福味道,当时浑然不觉,如今想起,甜得扎心。哦,我的泥屋新娘,我的独角牛,这一切都和你们密不可分!
村里轮流使牛,生小牛那天恰赶到她家。一村的人都跑去看,他注意到,一大半的人头都扭向她。脖上系着的红纱巾把她的眼衬得像天上的星子。他的眼睛不够用了,看一眼小牛,再看一眼她。老牛呢,谁都不看。甚至顾不上看一眼小牛,只顾低头吃干草。那是他从草堆扯来的,他心疼它,怀着小牛照样犁田,现在,它像卸货一样卸下了肚里的小东西,肚里瘪了,神情松快,大眼沉静,悠远。他惊奇地看着老牛卷起干草一下一下慢慢反刍,世界真奇妙,灰黄如土的干草能化为乳白的奶汁!老牛咀嚼干草的样子极庄严,像在咀嚼它的前生。他也扯了一根草,放在嘴里没嚼两下“呸”一声吐出,他嚼到的是灰尘与草渣。
为这一抱干草,她当众夸了他,说他糍粑心肠,是阿弥陀佛一个人。一句话让他的心生了羽翅,飞向云霄。
……
作者简介

陈家萍,中国作协会员,合肥市拔尖人才,研究馆员。著有长篇小说、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说集六部。中短篇小说散见《莽原》《时代文学》《安徽文学》《海燕》《当代小说》《伊犁河》《六盘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