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1-13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
期刊名称 |
发表期数 |
作品名称 |
体裁 |
|
《中国铁路文艺》 |
2021年第2期 |
净心抱冰雪 |
散文 |
|
《火花》 |
2021年第3期 |
金木苍凉 |
散文 |
|
《作家天地》 |
2021年第4期 |
关于冬天 |
散文 |
|
《中国作家网》 本周之星 |
2021年第11期 |
烟火探微 |
散文 |
|
《牡丹》 |
2021年第4期 |
水痕 |
散文 |
|
《短篇小说》 |
2021年第4期 |
表叔 |
小说 |
|
《奔流》 |
2021年第4期 |
看取星光逐水来 |
散文 |
|
《散文诗》 |
2021年第5期 |
看取星光逐水来 |
散文 |
|
《太湖》 |
2021年第3期 |
无如挂碍 |
散文 |
|
《火花》 |
2021年第6期 |
人间烟火独微如 |
散文 |
|
《中华文学》 |
2021年第4期 |
无缘缘 |
散文 |
|
《火花》 |
2021年第8期 |
灯影里的壁虎 |
散文 |
|
《躬耕》 |
2021年第9期 |
秋天的记忆 不识春光四十年 |
散文 |
|
《延河》(下半月) |
2021年第10期 |
小五 |
小说 |
|
《厦门文学》 |
2021年第10期 |
野塘籍春草 |
散文 |
|
《北方作家》 |
2021年第6期 |
手边上的光 |
散文 |
|
《石油文学》 |
2021年第6期 |
长取新年续旧年 |
散文 |
|
转载入选 |
|||
|
《杂文月刊》 (文摘版) |
2021年第7期
|
土狗 |
小说 |
|
《2020中国精短小说年选》(精短小说杂志社) |
2021年 |
回家过年的鞋子 |
小说 |
|
《思维与智慧》 (文摘版) |
2021年第36期
|
田埂的底色 |
散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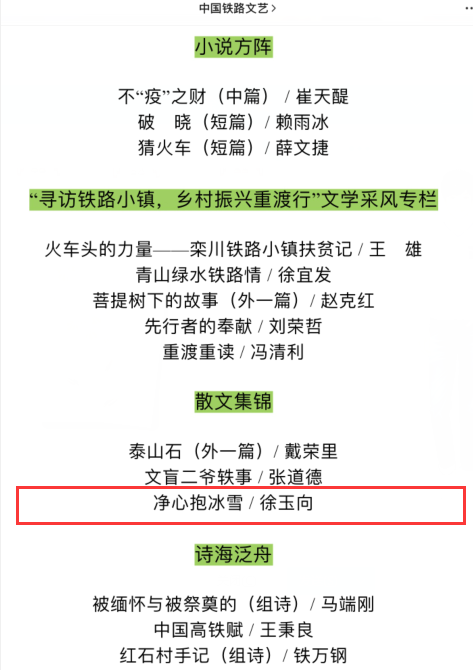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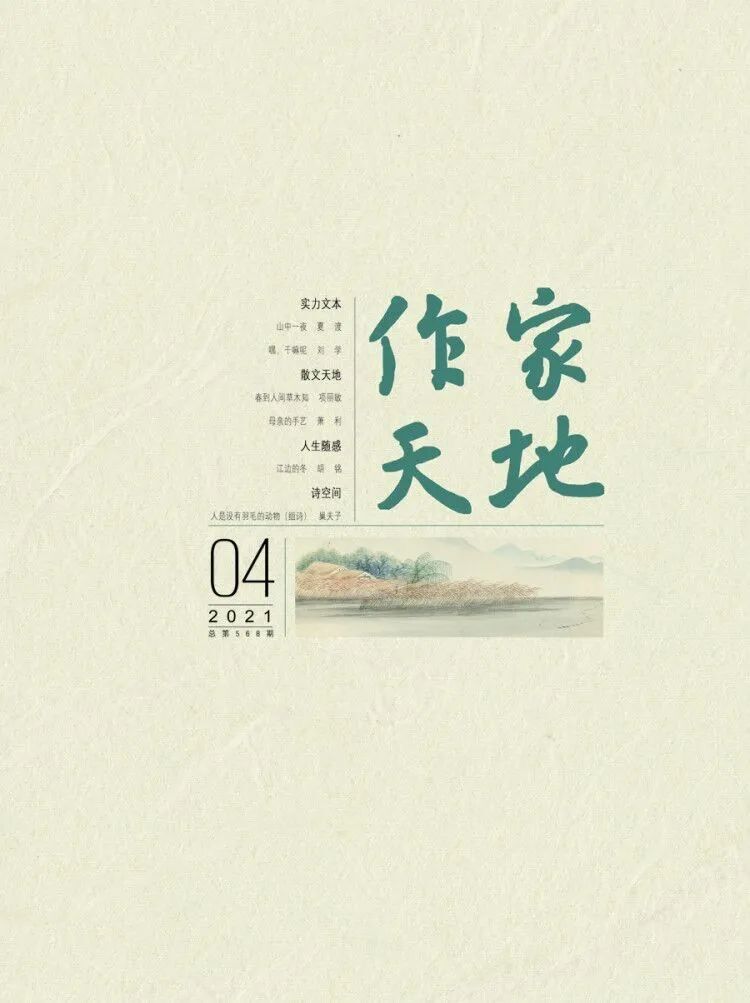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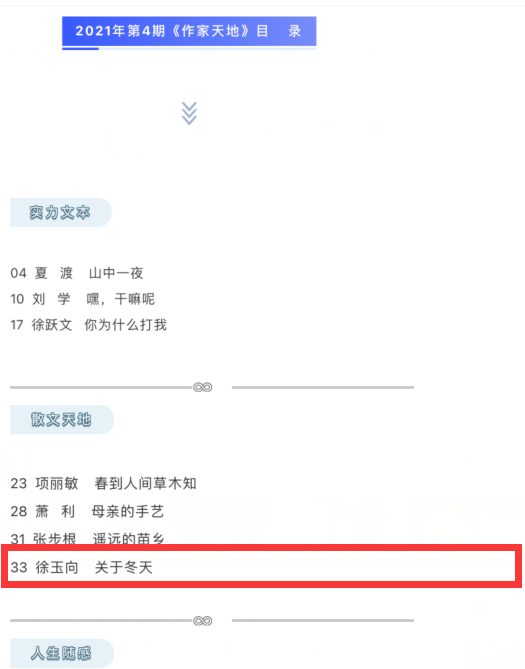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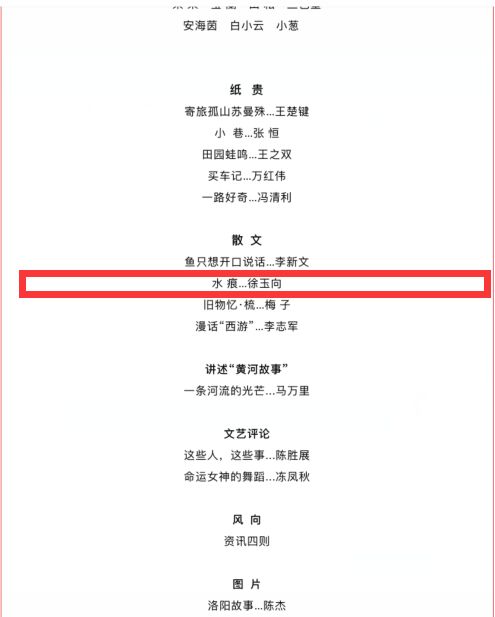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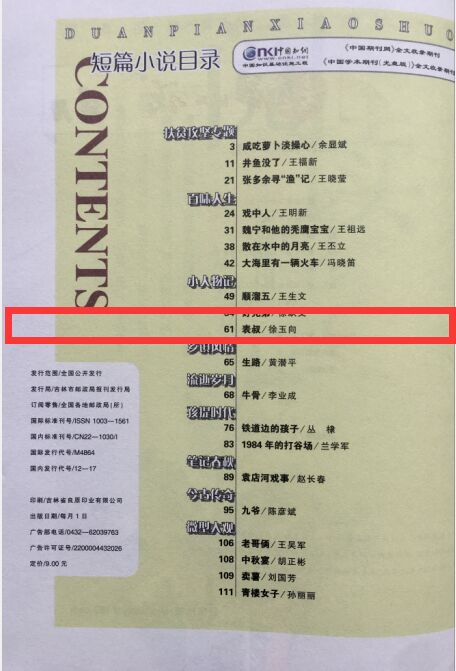
作品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