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6-12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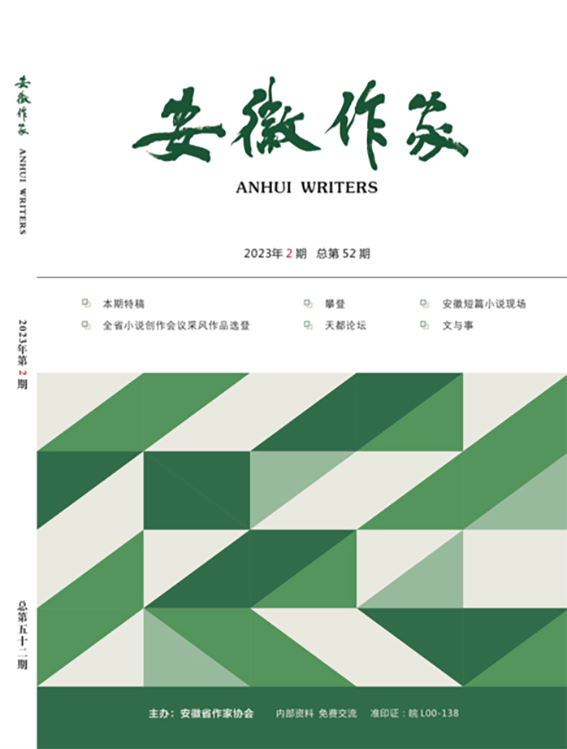

编者按:中国作协推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来,省文联指导部署,省作协积极组织,协调引导,搭建平台,赋能皖军文学精品生产,推动安徽文学高质量发展。本期《安徽作家》“攀登”栏目,刊发储劲松、程保平的作品。
作品欣赏
老洪琐事(外一篇)
程保平
一
此前,我曾远远看过洪哲燮先生。那时我上班才几年,是电台的一个小记者,一颗刚长圆的小青瓜。而他是报社副总编,我眼里的大官,一天到晚都绷着脸,眼光如刺刀,行走急匆匆,心里却总想着事。这让我发怵,觉得离远点好。
1987年深秋,天还有些热,某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洪哲燮,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八杆子打不到边,会有什么事呢?但我还是乖乖地去了。一见面,他就直接问,有女朋友吗?我老老实实地说,目前没有。他又问我家的情况。我说,家在农村,兄妹五个,我是老大。他说,有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好,我介绍给你了。一副没商量的架势。我不置可否,算是尊重,也算认可。但后来见没见面,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对方一听我的情况就吓跑了。
我当时觉得,这做法怎么说都有点欠妥。但后来发现,这是老洪一贯的路数,凡事亲力亲为,一杆子到底。比如他当报社总编时,站在大门口抓考勤,卡着手表对迟到的人说,你又迟到了几分钟。再如开全体职工大会,某副职喝酒进来,他指着鼻子说,你又不想好了吗?还有个小记者,瞒着单位偷打结婚证,被他发现,当即被派到服务公司钉了大半年的广告牌。
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报社曾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从政的有孙晓红、吴凤莲,后来都做到了副厅级。从文的有凌代坤、唐旺盛、李云、顾策,都成了有影响的专门家。没离开的人中有不少也是一顶一的,至今挑着报社的大梁。他们或是从老洪手上进来的,或是受了他的某些影响。报社原副总编董俊淮曾跟我在一个办公室编了几年的新闻稿,是一个温和、持中的老哥,多年后谈到日报,他说,报社总编好当,老洪早把架子搭好了。
退休后,老洪常到我办公室来聊天。我问,当初你做总编,把许多人都拒之门外,就不怕遭人忌讳,被穿小鞋吗?他一笑说,还真是。一次,市委孙书记介绍个人来,我看是学理工的,想都不想就回绝了。后来那人再找孙书记,孙书记哈哈一笑说,老洪就是那样的人,再换个单位吧。说到这里,他后悔地说,那时候真不懂事,再怎么着也不该挡着孙书记。
二
我被老洪领导过,但没在他手下工作过。除了那次见面,大约有十多年我没跟他搭上腔。后来我写了一篇稿子,是关于陈独秀的,登在文联的刊物《五松山》上,老洪看到,少有地夸了我好几年,弄得我心里虚虚的。但也心存感激,现在没几个人把文学当个东西,有这么个热心的前辈在前面顶着,对本地文学圈来说,总是一桩幸运的事。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渐渐走近老洪。一月或半月,他会到我办公室来走走,不客套,抽抽烟,问问近况,说点文学,感叹韶华不再,往往能谈一二小时,走的时候满地都是烟灰。令人讶异的是,他的聊天内容新鲜,就连“躺平”这类新词比我知道的都早。不像有的老先生,几句话一说,我就觉得是上世纪的人。
老洪退休后,作协换届,经主席团研究,聘他为名誉主席。外地有作家过来,我偶尔也请他陪陪。铜陵习俗,饭前要打几牌,每到这时,老洪就摆摆手说不会,然后坐在一边想心思。作为写作人,我其实知道,他又在如切如磋,推呀敲的,构思某首诗了。为此我十分惭愧,不把时间花在写作上,能弄出什么玩意来?
老洪年轻时是诗人,后来从政放弃了写作,退休后又捡起了诗歌,搜肠刮肚,笔耕不辍,这十来年里出了三本诗集。我也见过,有人退休后立志创作,但写着写着就写丢了。这当然不是坏事,人就一辈子,怎么快活怎么活,但那是普通人的快乐,而老洪却愿意做一个不普通的人。
可是,做这么个人谈何容易?就说写作吧,有几部作品能穿越时光的魔障,在千百年后直达人心,让人在通感的同时,而感激涕零呢?作家潘军曾伤感地说,我也写了几十斤书,不就是想如唐诗那样,在后世留下一二行么?不知道老洪是否纠结过。
三
退休后的老洪身上少了杀气,显得云淡风轻,但一直注重形象。他来我办公室,多着深色衣衫,有暖色条纹时尚而热烈地变化着,说话在和气随便中,却依然节制和机警。一次我求教说,作协要换届,主席出力不讨好,我不想再干了,您看谁合适?他默默看我一会儿,又转移谈别的话题了。
跟老洪在一起聊天,时局有重要的分量,比如疫情、民生、市政、中美关系、社会思潮等,他还是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气概,但不同于很多退休官员,他的思考不是标准制式,而是自己的,其中很多观点深邃而尖锐,这对一个一生做新闻、抓意识形态的官员来说,真是一个特别。
当然也谈文学、文坛、诗歌、文学动态,谁出了诗集等等,但具体到某个人某首诗,由于观念不同,又由于不写诗,我常有躲闪。一次,说到海子,我说,我跟海子年龄接近,文化背景接近,读他的诗有一种通感。他反问,海子那叫诗吗?
这事我后来想了很久,最后就想到了天花板。每个人都有限制,成长的时代和地域,教育的背景和阅历,相互作用后,会形成固化的价值评判。一方面当然是好事,叫成熟,有尺度,但另一方面又是天花板,以老眼光看新问题。它提醒我,此后无论是人生还是写作,都须有开放和包容的心理。跟长者在一起,既长教益,又有警醒。
还有就是谈孩子。每次见面,他都会问问我孩子的情况,自然会夸夸,又说到自己的孙子,刚开头又匆匆打住,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手里怕碎了的神情,总让我动容。老洪年轻时忙事业,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以致孩子没达到他的标准,就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然而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总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为此他一直纠结。
有一年,江西美术出版社总编陈征来铜采风,老洪和我们几个陪他上九华。在九华佛学院,院长藏学为陈征和老洪分别题字。一看到自己那一幅,老洪的脸色顿时大变。那题字是,舍得放下。
有道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若以此来概括老洪的一生,我觉得贴切,但也是这种入世的心理,让他有一个个牵挂,左右不能割舍。那次藏学是第一次见老洪,那是误打误开,还是拨云见日,我不清楚,但老洪那表情,在旁观的我看来,是华山论剑,云淡风轻中,有刀光剑影的惊心,也有被识破玄机后的尴尬。
四
老洪去世后,我告诫自己,不写他了。那原因复杂,比如他的特立独行,容易招来非议。再如接触不多,我不一定能懂他,写不好会画虎类猫。最主要的是钱钟书那句话影响了我,你要知道作者吗?那你去看他给别人写的传,他传就是自传。我怕一不小心露出猴子屁股,进而连累了老洪。
周末,我一个人在家练毛笔字,写着写着,就想到了老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我仔细思量,他的砥砺而为,特立独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来我是无意的,甚至是审视和保留的。但现在却觉得,不仅对我,也对时代和苍生,都有某种示范或指标的意义,不能就这样随着他的故去而流失、淹没了,我便改了主意。
董俊淮先生有不少时间是在老洪手下工作的。老洪去世后,他专程从合肥回来吊唁。我去看他,他讲了两个故事,一是老洪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时,规定公车能私用,但要有理由,比如家里出大事,同时都得缴纳汽油费。老董认为,这在当时是人性化操作,又兼顾了工作制度。再一个是有次出差,老洪和他等四人要在路上用餐,老洪点了四道菜,每道菜只要半份,惹得服务员直瞪睛,结账时只花了40多元。
五
老洪这次病情来的突然。6月2日,他外出散步,可能是行吟,这是他惯常的路数,回家后腹部不适,就上医院了。门诊医生说,天热,可能是中暑,回去喝点水,休息一下就好了。哪知病情越来越重,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医院,已经不能行走,直接被推进重症室。一查,是重症急性胰腺炎,一种非常凶险的病。
6月20日,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老洪病危,正在转往合肥治疗,他要我看看。原来,老洪跟省作协主席许春樵是忘年交,常有联系,那几日,许发现老洪没声音了,就几次追问情况,没有得到答复,只好到处找人,这才联系上了我。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老洪浑身插满管子,目光游移,只顾喘气,像一床破败的旧絮,觉得此行凶多吉少。其实到合肥也是没得救,院方说,准备后事吧。家人就护着老洪回到铜陵。当天下午,老洪去世,享年78岁。
午间我跟几个朋友小酌,说到老洪,大家都伤感。我说,所谓四十而不惑,简直是扯淡,人生惶惑四十始。比如老洪一辈子砥砺前行,毫不松懈,结果还是水过无痕,连作品都将不免。即使作品得以传承,跟他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人活在这世上,只能是不亏欠每一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们同意我的意见。
戴聪行状
一
戴聪去世已经满七。这些日子,有关他的信息渐行渐淡,以至于无,不由让我产生错觉,他是否真的来过。
我今天在家翻箱倒柜,只找到一根镇纸,三个红包。镇纸是戴聪去年在外旅游时带给我的,当时我正在练书法。红包他倒常送,有二十来张,是他手工制作的,我没当回事,送人了,只剩下这三张。他还为我做过几个木制墨盒,我同样没当回事,也送人了。我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他竟然走了。
戴聪还送过我几次土花生、菜籽油,说是家产的,不花钱。我不收,他就改送太平特产臭干,每次来我办公室,都带三二十块,我送不了人,只好自己吃,往往要吃很多天。这种见客不空手的习惯在农村常见,但在城里却失之于繁琐,可见他是以乡村伦理待人的。
戴聪送我这些,也算顺便。他每年编两三期文学小报,是自掏腰包,自写自编的那种,刊名叫《星雨》,刊载一些他的文字或书画,有时也介绍本地文学动态。他印好了,就上门送人,我当然是他要送的人。
我曾苦心劝戴聪,你一年收入才四万多,要花一半来印小报,不如攒了钱正儿八经出本书。即使出书,也不能当饭吃,不如趁年纪不算大,找一个女人过日子。戴聪说,我没班上,也娶不到老婆,不干这个还干什么呢?不知道是文学慰藉了他,还是坑害了他?
二
戴聪到我办公室大骂,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又仿尼采的话说,如果见到女人,请不要忘了带上你的皮鞭。我问,你有母亲、姐妹吗?回家跟她们说吧。他一愣,说,她们怎么一样呢?
这是30多年前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机关里乡下人,除了一张招摇撞骗的文凭,概无足道,除了寒风拥抱我们,其余皆无。那天晚上,戴聪是去相一个女人,未果,就找我来抒怀。我当时也失恋了,心烦,就斜刺一枪,不是有意要伤害他。
那时候其实跟现在差不多,人情似纸,恋爱与结婚,都讲家庭条件。戴聪出身农村,兄弟姐妹七个,穷得叮当响,这不由得让他的恋爱屡受挫折。深层的原因可能是长期养成的自卑,谦和与下气都是装出来的。但他又是诗人,崇尚罗曼蒂克,而且写诗有了点名气,实在憋不了,就露峥嵘,以至于动嘴或动手,这又导致了人们对他激进或不成熟的印象。戴聪的同事关系并不好。
忽悠到三十多,戴聪终于相上了一个女子,对方也没甚意见。不想,女方父母到戴聪单位打听,一问事情就黄了。戴聪生气,狐疑,猜忌,到后来,就是跟同事与领导的正面冲突。他彻底地被崩溃了。
戴聪被哄到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半年,这一下算是彻底断送了前程、婚姻和生活。那时候,精神病人好比脸上刻了道金印,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假如单位领导宽容一些,细心一些,疏导一写呢?我曾这样猜测过。
三
戴聪出院不久,就办了病退手续,回到了老家太平乡。好比远航的船,原是寄托五彩梦的,不想被海浪狠狠打了回来,成了一只破船、废船,这不仅让戴聪,也让家人不能面对。跳龙门呀,怎么跳成了这样?平复一段时间,戴聪似乎变了,气色红润,言行平和,说话也坦荡多了。农村那种简单淳朴的生活其实挺适合他。
我有几次去看戴聪,简陋狭小的楼上,他住二楼两小间,里面杂乱放着些书籍和纸墨,楼下住着一个残障的弟弟和老父。母亲去世多年,这个家过去是父亲维持的,如今其他的兄妹都成家单过,就剩下这三个特别的男人。戴聪没办法,每天都要面对油盐酱醋,缝补浆洗。我问,不烦吗?戴聪苦笑,有什么办法呢?
闲了,戴聪就写诗文,进步不大,主要是信息闭塞,但书画却进步不小,特别是书法,有娴静美好的气质。戴聪问我,是否可以在作协做点事?我是作协主席,当然能办到。后来就请他参加了一些采风活动,编编书籍什么的。为此他感谢不已,还送土特产给我。
戴聪去世后,作协秘书长告诉我,戴聪还有钱没领呢。我很生气,怎么拖到现在?她答,他坚决不要。原来,那两年我们编了两本书,有百把万字,请戴聪做校对,他一个个字地往前走,版面往往是一片红,而补贴也不过区区千把元。
戴聪病退后,其实日子一直紧巴。后来买车,要还按揭贷款,不得已,只好去做滴滴打车。因为不懂平台操作,有一次被运管处逮到,要罚款5000。那一次他是真急了,见我急得满头大汗,语无伦次。我是铁心要帮的,求爹爹拜奶奶,兜了很多圈子,才把事情弄平。
四
深夜,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让人心惊肉跳。谁在这时候不停当呢?一看是戴聪。我就问,是不是又罚款了?但对方说是戴聪的弟弟,他哥走了。我开玩笑说,是你们气的吧?他连说,不是,不是,是死了。
戴聪是在家做晚饭时突然瘫倒的,待家人发现,已是两小时,再到急救车开来,又是一小时。后来据说,他患的是心源性猝死症,到医院时还有很浅的呼吸。
戴聪去世后,家人希望搞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不然也太凄凉了。单位领导说,现在都不办告别仪式了。我当即表态,我们作协来做。告别那天,因为疫情的关系,人数有限定,大厅控制在五十人以内。我跟他一个弟弟说,作协的人要尽可能安排,他们来是送戴聪的。谁知发过入场券,到他家人,券却没有了。仪式结束,戴聪的那个残障弟弟撅着脑袋,硬是要往里闯,差一点动手打人。我质问工作人员,大厅都空了,怎么不可以见最后一面呢?那人说,这是规定,有事你去找领导。
我后来还是去了一趟戴聪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见一人。我上了那二楼,房间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四处找人,既没发现他的老父,也没发现那个呆弟弟。过去他们是由戴聪照顾的,离开了他,可能不方便吧?
我还记得,我曾送过几本国画技法的书给戴聪。我看他那无师自通的画法实在不入流,希望他练一练,也算宝刀赠英雄。我到处找,也没找到。不是我可惜书,而是想找点东西作纪念。
我坐在那房间里还在想,满七了,有没有人为戴聪烧点香呢?一个一辈子没结婚的人自然等不来儿女,但或许有红颜知己呢?真想他有此浪漫,也该如此浪漫。
作者简介

程保平,1984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散文随笔协会副主席,以专攻散文为三余之乐,曾在《天涯》《钟山》《安徽文学》《作家天地》《新青年》《新民晚报》等媒体发表文字作品,出版个人专辑《徒然书》,主编文学作品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