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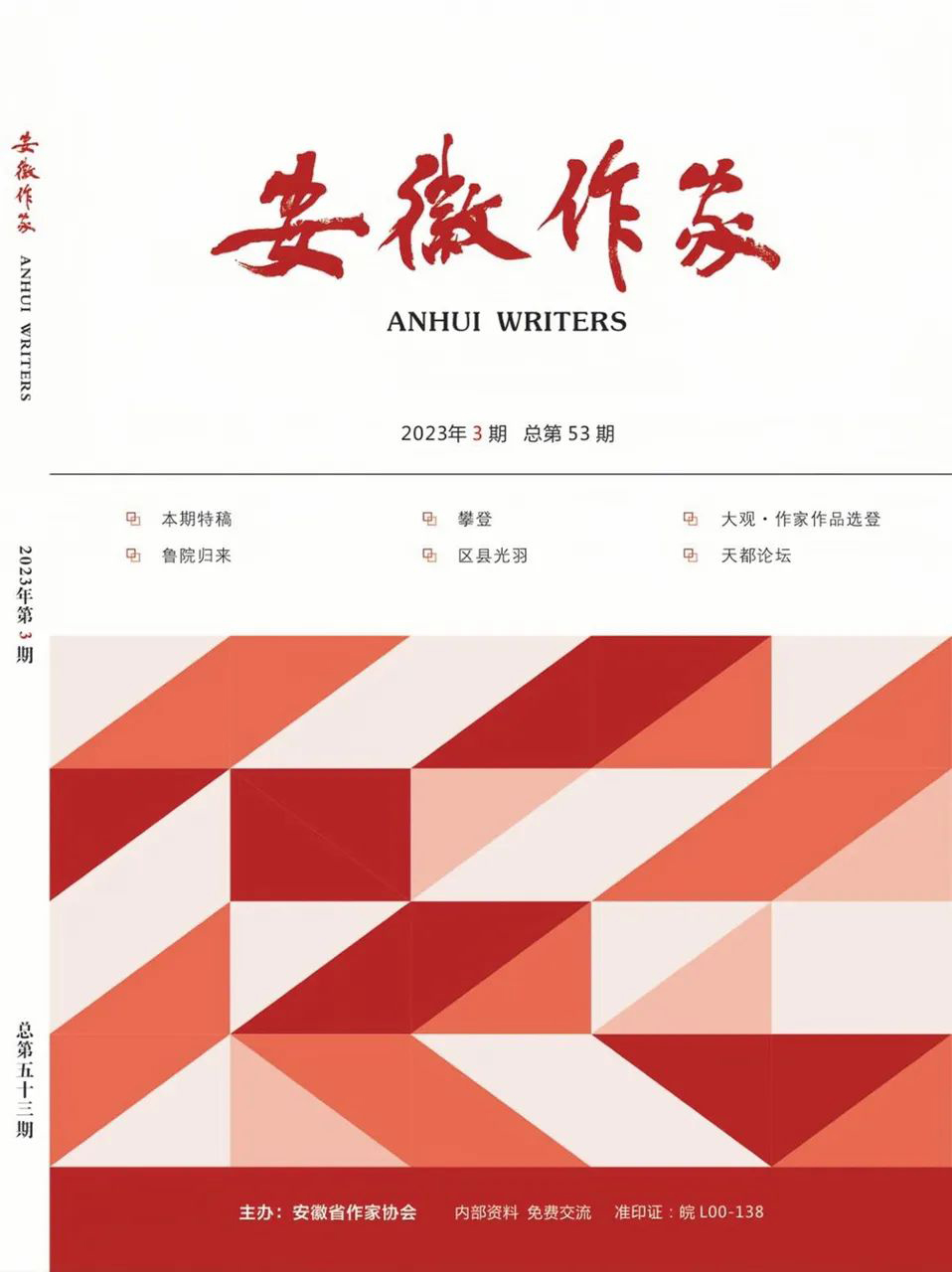
作品欣赏
张旭光
一
去旌德。一行五人,去采风。
旌德多山。远山的线条,像奔牛之脊,顶破一袭深蓝的棉袍。裂开的豁口上,洁白的棉絮漫作云海,浩荡而疏朗。那么多山,都默不作声,低眉的样子,谦卑、木讷、羞赧、沉静。斜靠在车内,陡然之间,便生出阅尽红尘、心归云山之感。旌德有古水,曰徽河。敢择“徽”而名,其人文定是不浅。
史载,唐宝应二年(763年),置旌德县。《元和郡县志》:“本太平之地,以县界阔远,永泰初‘土贼’王方据险作叛,诏讨平之,奏分太平置旌德县。”又《太平寰宇记》载:“冀其邑人从此被化,故以旌德为县名。”零星数语,这货真价实的千年古邑,瞬息便生出包浆气来。
车过之处,间或冒出些老屋。白墙黑瓦,檐牙高啄,仿佛哪位丹青妙手刚刚一笔天成的白描,墨色尚未干透。那些徽式建筑,不成群,零星地挤在沿途不算气派的新式楼房中,真实,苍然,清寂,突兀,凄美,清癯骨立,孤绝泠然。
久闻旌德负徽韵,这算是浅尝罢。
我想,去陌生的地儿,便做个陌生人吧。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想,慢慢地遇见另一个自己。人在旅途,很多时候都有种奇妙的心境。譬如,当你背着行囊在人海中匆行,忽然发现一个背影,恰似故人;当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遥望远山与村落,忽然越看越觉得这就是故乡;当你在遥远的海边,听见一只燕子呢喃着飞过头顶,忽然感到这就是小时候听过的那一只……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旌德,注定与我、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又行半盏时间,车子抵达旌德江村。我猫出小车,放开身子来。此时,青山卧水,白云补天,和光融融生暖。随意扫视了一眼,这村子,懒懒散散,吊儿郎当,透着股久经沙场,惯看秋月春风的味道。
二
下午,走江村。果不其然,老得很。苍古,散淡。
江村风雨近1400年。据记载,南朝杰出文学家江淹,也便是那“江郎才尽”的主角,曾知宣城。后,其五世孙江韶,择旌西金鳌山族居,始得“江村”一名。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江村丰厚的人文。如今,徽河东去,浪淘千古风流。那些名人巨子都作了风烟,尚余古塔、古碑、古祠……以及那些已厚植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传奇与故事。
然而,我想避开他们,仅仅走走我的江村,专拣那老街深巷走过去。
这些老街小巷,闹就闹到沸反盈天,空就空至死寂。逼仄的老街,商店、肉铺、茶馆、酒肆、马扎、摇椅、案板、箩筐、木梯……都散落两旁,毫无章法。挂霜的老人,追逐的稚子,穿针的妇女,赤膊的壮汉,吆喝声,哭闹时,呱天声,磨刀声,炒菜声、烧水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感觉安稳、散淡。在这里,你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不急不赶,不争不斗,就那样卸下生活的包袱,懒懒散散地过日子。这是我们在努力挣脱,又无比向往的生活,这是我们用来存放另一个自己的地方。
小巷寂寥。出得老街,一拐,便是幽深的巷子。这是一个古老、空灵的境地。那些青条石板,随意拼接着,像远古恐龙的肋骨,淡定、安素。轻轻地走,一定要轻轻地走。走着走着,有穿青衫的人撑油纸伞迎面走来,有挎着竹篮子梳麻花辫的卖花女子走来,有打马悠悠晃晃哒哒穿行的诗人迎面而来……你还看见自己在放下手机、电脑、应酬、疲惫,靠在老墙上,看星星与月亮。
巷子没尽头,就像我们心灵的渴望没有彼岸一样。踏着高龄的青石板,我多想将这静谧的时光封印在脚下,等下一个有缘人来,读我。
……
心 灯(节选)
张万林
一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从外地坐晚班车回到县城,已是凌晨二点多钟。外面寒气逼人、冷气刺骨。借着路边昏黄的灯光,隐约能看见草木结霜。
我经过县城两个农贸市场,一大一小。却看见里面灯光大亮,车来车往,里里外外都有人忙个不停。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呵着热气,忙着装菜卸菜。
经过街道边,有的店铺门还是开着,说明店里可能在营业,也可能是忙着即将到来的早点。
我也在地面结冰的早晨,看见环卫工人用扫帚“沙沙”地扫地。或是一些年纪大的环卫工人,提着一桶水,用抹布一下一下地擦洗着气味很重的垃圾桶。
我更看见无数的工地上,无数尘灰满身的建筑工人,一脸黑糊地忙个不停。我也看见一个个巨大的车间里,抬眼望去,是黑压压的流水线人群。
我常常想起母亲晚年时,一个人在家乡居住,一个人住在一大套房子里,一个人烧饭,一个人吃饭。进门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我们才驱车几百公里,跟她过上几天热热闹闹的日子。
但我母亲忧愁的时候很少,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大声地说话,大声地谈笑。而且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每天也收拾得清爽整洁。在母亲的身上,我总是能感受到一股精气神的存在。
我曾经写过一个没有上过学、读过书的女性老人,用一生的时间把几个儿女培养成人了,几个儿女都很优秀、也很孝顺。
老人六十岁时,在地方老年大学食堂里帮忙烧饭,看到一群与她年龄相当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学画教画,她也想学。她的兴趣得到了老年大学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也得到了自己子女们的全力支持。七十岁那年,她在我公司里编印出了厚厚的一本、署有自己名字的画集。
这个真实的故事,我讲给我妈听过,把她的画集拿给我妈看过。也讲给身边的很多人听过,把她的画集拿给身边的很多人看过。
故事还没有完,在她的画集还没有印刷出来。她在外旅游时,被一棵上面掉下来的树枝砸成了几近植物人。自己辛苦绘画、编印的画集,直到一年后,她清醒过来了才看到。
后来,听说她恢复的很好。
这样一个一生没有读过书、识过字,一生打工养育儿女,六十岁才学画画,七十岁印刷自己的画集,后来又昏睡近一年时间才醒过来的老人。我好像看到,这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人都和我的母亲一样,心里都有一盏为自己点亮的心灯。
二
我一直记得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老师书中的一句话,他是这样去诠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努力向前走。他说,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个人有如江海大河中的一粒细沙。我们大家密密麻麻、随波逐流地挤在一起,被时代的大潮推着向前走。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比较辛苦、比较逼仄。我们走着走着,有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天感到累了、倦了,实在不想走了,不想与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竞争了。于是就停了下来,选择躺平。
俞老师说,选择躺平很容易的。刚开始躺平感觉很舒服,没有了往日的辛苦追逐,没有了竞争残酷的压力,认为选择躺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还认为自己很“佛系”,与世无争,岁月静好。
关键是你选择不走了,不争了,躺平了。你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自己越来越沉到江海河流的底层。你只会越沉越深,因为还有许多与你同样想法的人,他们会压在你的身上,越压越多,越压越重,直至把你压进永不见天日的淤泥底层。等到哪一天你想翻身浮上来,想再去呼吸上面的清新空气,再去享受上层激荡的水流,再去观看远方的风景。你才发现,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
俞老师这段话一直有如烙铁一样,常常烙得我生痛。我一直记得自己人生中最至暗的两个十年,这个至暗的日子现在还一直是我的噩梦,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前一个最至暗的十年,我根本看不到前方路在哪里,我又该向哪个方向走才是正途。我看不到一点点生活的希望,我就像是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但我心里隐隐还是有股想法,知道自己必须不断往前走,如果不走,我就真的完了,真的沉入到最底层的淤泥里,在黑暗里永世不得翻身。
后一个最至暗的十年,我生意遭遇了瓶颈。几年间,又相继失去了我生命中血缘相融的两个人。那段时间,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需要我去解决和面对,有些事情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我又推不掉、甩不脱,我身心俱疲、焦躁不安,身体也出现带状疱疹。
后来我还是走出来了,如果不走出来,我可能再次沉入到生活的淤泥中。我看不到现在的一切,拥有不了现在所拥有的事业、家庭、财富和名誉。
……
小暑之后(节选)
倪光明
一
太阳终于在小暑之后,露出了灿烂的笑脸,香樟树叶上尚存的饱满的水份,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昨天的雨似乎疯了般,片刻也让平地起水流淌。那雨声嘶声力竭,我在想远方长江沿岸饱受梅雨之苦的朋友,你是否一切安好,我拨好了电话号码,又怕是多余的眷顾,让彼此良好的心态,徒添许多烦恼。
这个清晨,布谷鸟的声音从西南水杉林中传来,从音贝上分析是两只布谷鸟,一只声音饱满,一只略显纤弱,这分明是一对求爱的男女在对歌,但我不知道它们彼此唱的内容,它们是否“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在思绪中,这个早晨,村庄一片寂静,因为有这么一对恋人,村庄便有了声音。另一个声音来自我的床边,是豢养多年的老狗,睡梦中发出一阵阵呻吟——我相信这是一种惊慌的呻吟。有人说十来年的狗,相当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我看看它,它还睡着。狗能做梦吗?我不知道。书上说,狗的智商相当于三,四岁的小人,三四岁的小人会做梦吗?它的梦是否与我一样,渴望自由的翅膀?
二
小暑之后虽然晴了,天气预报说十点钟又要下雨,几只没有脑子的蝉,在高高的树梢上拼命的鸣叫,毫无逻辑地重复单调的歌儿,把我正在思考的思绪打乱了。真想找只竹长杆,去驱赶这些讨厌的蝉儿,之后想了想好笑,原来以为自己是有修为造诣的,其实也就这么一点啊!你和这些节肢动物怄什么气?黄莺在三角枫枝头,追逐恋爱,它们撕打着,欢叫着,让人猝不及防。麻雀在小灌木丛里窜来窜去,叫声短促又琐碎,也缺少逻辑又急于表白,像我家门口三喜的老婆每天都叽叽喳喳,不晓得讲的什么。
村庄鸣奏起欢快的大合唱,只有蝉唱着不和谐的声音。其实我喜欢秋虫的声音,静静的夜,纺线婆婆与蝈蝈的鸣叫,节奏欢快又悦耳,如果驰骋你的想象力,那真叫天籁之音。我不知道那蝉是如此的撕心裂肺,这钢铁般的坚强而单调的逻辑,仿佛是个男性的忍者,让人闻而生畏。
这两天有点异常了,往日里每天必到的喜鹊不见了踪影,是不是昨天的疾风骤雨,摧残了它的老巢,整个空间没有了它那傻大姐一样百无忌惮的叫声,那样优雅,欢快,清新,和睦。偶尔失去了它的声音,未免惆怅起来。好在门前池塘里的莲花持续数日开放着,昨日的雨虽然让它们看上去憔悴了许多,在莲花下面的莲叶上,两只蛤蟆摞在一起交配,似乎把它们丑陋的基因永远传承下去。雨后,阴凉,湿润,惬意得很。
……
(原载于《安徽作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