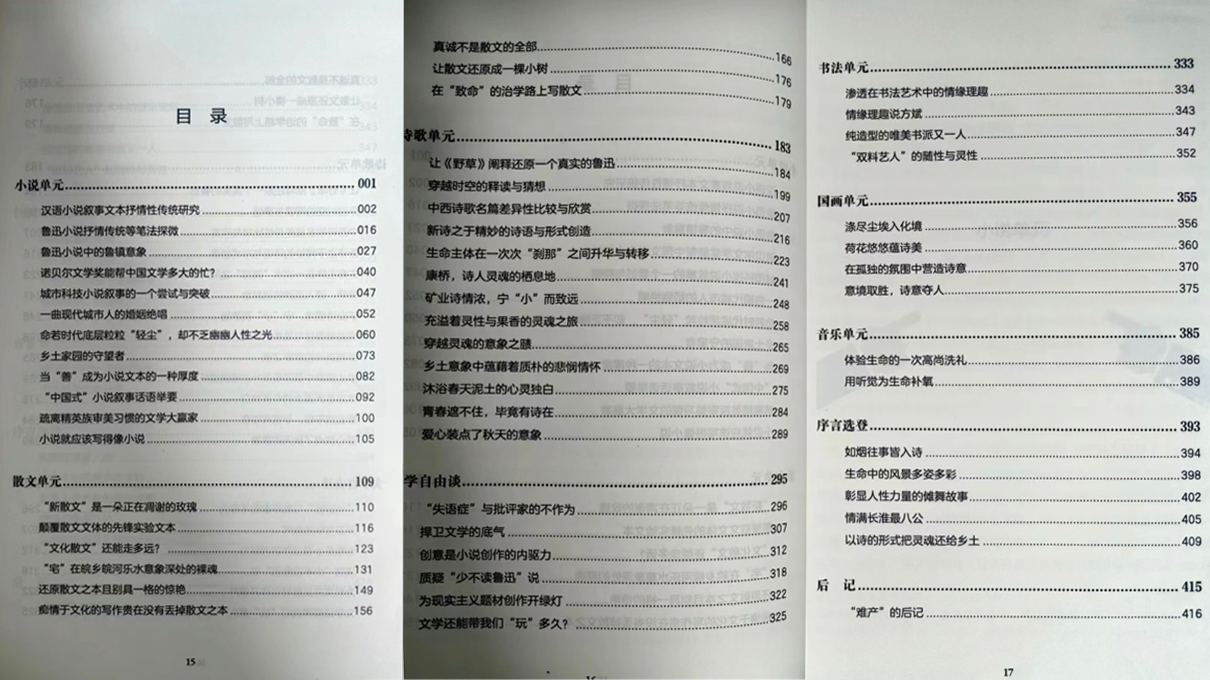从本土文化语境和意境审美形态去考察鲁迅小说文本,既有助于更客观、更准确地理解其人其文尤其小说作品的某些思想和意义,也更有助于体现“以中释中”的话语习惯和释读原则。“以中释中”就是从本土文化渊源和审美观念的角度去释读鲁迅小说文本。无论鲁迅写小说是借鉴国内外哪些小说家及其小说文本,都不影响我们“以中释鲁”或“以鲁释鲁”,因为鲁迅毕竟是汉语的“这一个”,其小说文本也毕竟是汉语的“这一种”,所以鲁迅及其小说和我们是心心相通的。作为汉语的“这一个”,鲁迅无疑是使用汉语写作的典范,无论是情境还是社会文化语境,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制约着他,这也与他的生存习俗及其生存模式息息相关。作为汉语的“这一种”,鲁迅的小说文本,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叙事审美形态,无疑都渗透了这种文化语境乃至意境理念的“基因”。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就是一个渗透了鲁迅自身文化审美观念的意中之象(即意象),被鲁迅“意中”的这个鲁镇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坏境,鲁迅笔下诞生的每一个典型性格都与鲁镇的文化血肉相连,无论阿Q生存的未庄还是“我”与吕纬甫、魏连殳、以及车夫遭际交往的S城,也都被覆盖在鲁镇文化的“麾”下,鲁镇的文化语境业绩也就决定了鲁迅笔下的人物性格差不多都被“定格”在“鲁镇化”的语境之中。说得更确切一点,这种“定格”就是一种文化习俗、生活模式的“定格”,也是一种“集体习惯”的“定格”,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滋生什么样的文化性格,这似乎也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及其规范。不过意象之于本象是一种超越,虽然鲁镇就是绍兴的代名词,但我们以文学的规范说法,鲁镇又不等于绍兴,他是经过作家思考、沉淀以至命名,是被艺术化、理想化了的一个世界,他虽然魂系绍兴,却又是梦中的绍兴、模糊的绍兴,是被形而上思维高度抽象化了的一个边缘无限宽泛、却又要收取门票的特定世界,不是什么人想进来就能进来的世界;既然是“意中之象”,凡是能进来的人物形象也应该是作家艺术世界中的意中之人,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以及吕纬甫、魏连殳、包括那个车夫等都是作家的意中之人,作家往往不请自到。鲁镇就是鲁镇,他只姓鲁,而不姓赵、钱、孙、李。它是江南水乡,又是两千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封地”。它是鲁迅独有的意象的生产“基地”,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是艺术的天堂,又是生活中的“黑暗王国”。你无论是从孔乙己走进鲁镇,还是从祥林嫂走进鲁镇,似乎都能领略到“咸丰酒店”的虚荣以及鲁府、赵府、钱府等大同小异的风格极其某种象征意味。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像远在天边的陌生世界。所以说,鲁镇是鲁迅对于绍兴的一种超越与抽象。显然,文化语境对于小说叙事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要真正了解鲁迅其人其文,首先就要了解鲁镇的文化背景以及语境,正是鲁镇文化语境成就了鲁迅笔下的鲁镇意象。的确,要了解鲁迅小说之象,就绕不开鲁镇之象;要了解鲁镇之象,又绕不开绍兴之象。只有深入绍兴这个真境才能梦入鲁镇这个虚境,从那里去探索、触摸鲁迅及其笔下各种人物的“心跳与脉动”,才更有利于我们不偏不倚地认识鲁迅、释读鲁迅、把握鲁迅。如果说鲁镇之象就是国象民态的缩影,那么鲁迅笔下涌现的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一个个国象民态的缩影。的确,国大多象,险象环生,在鲁迅艺术构思中都逐一被还原成了一个个典型形象,这一个个典型形象聚沙成塔——凝聚成一种创作思想,即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之大义。故此,本文立意之所以强调从本土文化语境及其意境层面去释读鲁迅小说文本,就是回归“以中释中“的话语路数,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把握鲁迅小说的本土文化情结与脉络,我们也就能更加深刻地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及其地域性。诚然,我们越是从本土文化语境说,我们也就越容易走近鲁迅、越容易触摸到鲜活的鲁迅,如此,鲁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也都会跟着鲜活起来。“集体无意识”理论虽然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在鲁镇也存在“集体无意识”文化形态,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就是鲁镇集体的记忆与沉淀,是鲁镇与史俱来的一种文化滋生了这些“鲁镇化”了的人物,我们也可以套用歌德的那句惊世之语:不是鲁迅创造了孔乙己、祥林嫂、阿Q,而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创造了鲁迅。与其说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创造了鲁迅,还不如说是鲁镇的文化语境创造了鲁迅,因为那里是鲁迅精神的出入口,阿Q们一个个从那里走进来,又一个个从那里走出去。文化语境成就了小说,小说成就了鲁迅,鲁迅到头来又批判了阿Q们的不觉醒,以唤醒阿Q们知道地上本没有路,只有勇敢地去走、去闯,才有希望成为路。无疑,在鲁迅的鲁镇意象中,象是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这些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象,被演变成为一个又一个鲁镇形象,他们既是文化语境的产物,又是意中之象的升华,意象与文化语境都在作家的构思过程中发酵,最终构成一个个复合体——即一个个被深深打上鲁镇文化烙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文化语境所拥有的能量不断给作家输血、充电,使其“造人”自如;否则,断血、断电,作家的意中之象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舵之舟,如此,还遑论文学创造?可见,鲁迅笔下营造的鲁镇意象是被本土文化语境“定格”了的集体记忆与沉淀,“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①杨义的这一论断可谓一语中的、切中命题之要义。不久前曾浏览过邓晓忙的《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不禁与之产生一种共鸣。从生存意境层面去考察一代小说家的“灵魂之旅”,似乎也给本文的立意与行文提供了一种依据乃至模式。本土的文化语境与生存意境的本质意义是相通的,强调的都是“以中释中”的话语模式。就鲁迅小说叙事形态而言,本土文化语境与意境审美观念都被凝聚在了鲁镇意象之中了,语境与意境息息相通,可以说是语境生发意境,意境又观照语境,这种关系在鲁迅的艺术构思中就成了鲁镇意象的内质。所以,我们释读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不能绕开语境与意境的双重文化背景,也就是说,鲁迅小说的生存语境与意境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文化背景,也只有在那种文化背景之下才能营造鲁镇意象,才能塑造出诸多以阿Q为代表的鲁镇群像。可见,饱含语境制约的意境审美观念的参与乃至渗透,又使得鲁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不乏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与内敛,可谓静水其外,流动深处,即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正如杨义所言:“叙事语言分析,在中国古代也是注意到了。“所谓‘春秋笔法’在相当程度上乃是语言的感情色彩和表义曲折性的细心选择。”②所谓表义曲折性的细心选择,就是典型的意境生存形态,或许,中国文学批评家只习惯于从诗词歌赋中去考察意境的生存审美形态,而很少从汉语小说文本尤其鲁迅小说文本去考察意境审美形态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应该承认,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的意境审美形态并非是中国抒情性作品的“专利”,自中国小说诞生以降,建立在本土文化语境基础之上的意境审美形态,就成为汉语小说的一种文本品质,这就是意境文化及其审美观念的参与及渗透,也就是让汉语小说成为汉语小说的一种文化标志抑或胎记。尽管鲁迅小说文本也多有“拿来”的痕迹,但小说文本从立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经过鲁镇文化语境的检测与浸泡,最终才成为鲁镇意象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鲁镇化”就是“中国化”抑或“民族化”,是对“中国化”抑或“民族化”的缩影集成,是由宏观转化为微观的“疗救试验地”。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鲁镇意象之“象”,可由大到小,一旦进入小说又自然发酵从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尤其含蓄的题旨与思想,也不乏“春秋笔法”——情也幽幽义也幽幽,这在鲁迅小说文本中也不乏其例,其表义的曲折性也就见其意境之境的审美意味了。不容置疑的是,释读鲁迅小说叙事文本,应深谙鲁镇意象与文化语境、意境诸元素是并存而互相制约的,尚若淡化这些元素去释读鲁迅及其小说,那么或许鲁镇就不成为鲁镇、鲁迅也不成为鲁迅了。《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就是鲁镇意象中的一个十分贴切的文化符号。据有关资料,鲁迅生前曾与人“自诩”《孔乙己》是他最得意的一篇作品,是他在一种极其从容的状态下写就的一篇超短精品。所谓“从容的状态”,可以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状态?比如“咸亨酒店”就是鲁镇特有的一个文化标签。它属于鲁镇,也属于孔乙己。因为孔乙己这个人物只有在“咸亨酒店”这种场合“挂职”,他才能成为孔乙己,否则他就不叫孔乙己了。从审美观念上说,《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文化风景就具有一种意境美学意味。小说开篇就把“咸亨酒店”的格局凸显出来,给人营造的一种想象空间是,——接下来要来这里“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一定是一个穿长衫的别样的“这一个”,果然,接下来迎“刃”而出场的孔乙己确定很特别。作者对孔乙己的一番描述就埋下一个伏笔,孔乙己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抑或某种文化的牺牲品,因为前面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文化平台——“咸亨酒店”本身,就算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暗示:见识一下穿着长衫来此一醉的孔乙己吧。于是,孔乙己的身世遭遇就被“咸亨酒店”这个文化平台“一览无遗”。横竖看去,鲁镇的“咸亨酒店”就是专为孔乙己的“落魄表演”而特设的,他的性格及命运似乎与鲁镇早已融为一体。“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这副形象特征描述,俨然诞生在鲁镇“咸亨酒店”的一幅活漫画,真乃人比人、似人又不似人呐!这种语境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却又站着喝酒,似乎很想在一群短衣帮面前做做人,可是想做人却又不像人,倒还不如脱去长衫混在短衣帮里面随便喝上几杯更本分。本来就是一个冒充的“阔爷”,却硬是要“排”出九文大洋。于是,便引来一片怀疑与嘲弄,赖活着还死要面子,结果导致他在“咸亨酒店”丢人现眼,出尽洋相,尊严扫地。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叙事,却让读者在不经意中触类旁通,即由语境逼出意境:是谁扭曲了孔乙己的人格?竟让他活得如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小说虽然没有直白创作动机抑或立意与题旨,但读者也不难透过字面给出自己的答案:一个原本进取的读书人如今居然落魄到这步田地,谁该为他买单?孔乙己实在是鲁镇的不幸!更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不言而喻,那个时代就不能让孔乙己这种人活得有尊严,因为那个时代的本身就没有尊严,俨然一个无形的大脓包!小说中的文化语境之重要背景就是直通兴盛于鲁镇的封建科举制度,正是这把无形的“封建文化”之“软刀具”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孔乙己给“戕害”了!“咸亨酒店”就是交代孔乙己穷途潦倒、生不如死的“文化载体”。小说中文化语境又依赖一种话语蕴藉滋生语言的张力,既运用话术把故事讲得比较含蓄,这样才能在意中生境,境就是一种空间,这种空间就是想象的空间,用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说就是“话里有话”。倘若叙事话语不能给读者带来一个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意境也就成了一个个“空头支票”。说到底,意境意识就是空间意识,意境美就是空间美,就是汉语小说在叙事中营造的一种“留白”效果,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不说,就像抒情诗作品比如诗那样含而不露、蕴意隐蔚,把含蓄的、超出字面的文本意义都留给读者去想象、去释读。尽管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小说叙事都离不开想象,其立意(即主题思想)也都深深隐蔚在人物形象的言谈举止之中,也可以说很含蓄,但汉语小说叙事中所渗透的意境理念,完全是一种语言习惯,不像西方小说叙事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想象的能力乃至天赋;而汉语小说叙事所呈现的一种意境审美形态,特别需要一种典型环境尤其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的支持,同时又借助于话语蕴藉的语感,在叙事中常常会产生一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话语效果,就好像每一篇小说叙事都如同在举办一场“中国谜语大会”,小说家每每讲出一段故事,其“谜底”就会不打自招被读者了然于心。有些话明明说得很含蓄、也很含混,而汉语小说的读者就能常常凭借文化语境的种种暗示而得以理喻乃至顿悟。所以,汉语读者阅读汉语小说,往往不需要卒读就能知其结局一、二,这或许就得益于语境的帮忙。如此种种特质,可能就是汉语小说区别于西方小说最本土的地方。鲁迅显然没有而且也不会跳出这种语境的“魔掌”,意境审美形态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示在其中。的确,在鲁镇“咸亨酒店”出场的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在那里重演活受罪死要面子的悲剧性格,其命运的结局也就被他自身的性格瘤给出了答案:孔乙己这种人肯定活不好,在封建文化缩影的鲁镇,就是孔乙己的葬身之地。这个结局在小说叙事中一直是含蓄着的,但在语境与意境的作用下,这个结局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并不神秘,读者知人论世,通过剖析鲁迅的小说主题及其鲁镇的文化背景,孔乙己的悲剧又要在鲁镇重演的立意,是不难破译的。 “在文学作品中,关于语义关系、关于意象、意境的探讨,关于心与物、神与形、情与理、意与象关系的理论等等,都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原型理论所探讨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叙事文学模式背后的观念等等,都表明了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立的原型体系和再现方式。”③这种从西方“集体无意识”抑或原型理论的说法虽然有“以西释中”的倾向,但与中国的文化渊源也有一定的互补性,前面已有交代,与其说孔乙己是鲁迅创造出来的悲剧,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那种社会尤其鲁镇那个特定环境集体“造就”出来的悲剧,单就这一点而言,东西方文化也有相通的一面。祥林嫂也属于鲁镇的“这一个”。鲁迅小说研究中,人们对祥林嫂形象的释读已经够多的了,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不仅语境作用其中,而另一个要素意境——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乃至渗透到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之中,并成为鲁迅小说叙事之审美形态中一个最本土、最鲁迅的文化特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鲁迅并非刻意地去建立意境文本,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叙述习惯和话语习惯的自然“撮合”。意境审美形态表现在叙事话语上,就是一种话语蕴藉,就是一种含蓄,只有做到叙事话语的蕴藉与含蓄,意境空间说、想象说才可以成立。在鲁迅为数不算多的小说作品中,《祝福》是最富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一篇,从标题的设立就可以领悟到一种语境与意境的魅力!在鲁镇,“祝福”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莫大的讽刺,已经成为孔乙己葬身之地的鲁镇,下一个就轮到了祥林嫂。讽刺的意味在于,鲁镇不是在“祝福”节日,而是在“祝福”一个人的死。死对于祥林嫂,的确就是“福”!现在文学研究者们似乎更看好沈从文、郁达夫、废名等作家小说叙事文本的意境层面,似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洋溢着一种立人思想),至于意境追求似乎就不敢恭维了。其实这是对鲁迅小说的误读。在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中,也同样拥有说不完的“意境”存在形态,正如方锡德所言:“在中国现代小说美学理论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审美范畴:一是典型,二是意境。典型学说来自西方,而意境则是最能显示出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审美原则。现代小说家对意境的追求,既是我国人文传统美学心理结构的顽强表现,也是抒情与写意传统中的最高美学原则对现代小说的渗透。”④由此可见,我们即使不说鲁迅刻意追求意境美学,却也不能排除意境美学悄然渗透其中的事实。限于篇幅,这里不必再展开分析释读《祝福》的故事情节,就语境、意境层面而言,《祝福》这篇小说的标题就很有张力,就像一首抒情诗的标题,立意彰显出一种充满苦涩的想象空间。在一个以礼教的名义扼杀、毁灭幸福与伦理的世界里扬起一面“祝福”的旗帜,透过字面从文化背景上去考量,“祝福”的曲包之意就预示着一种凶多吉少的悲情色彩。小说开头采取逆时叙的方式,推出“我”在大年临近之际所见到的祥林嫂,祥林嫂的一番关于死后鬼魂有无之迷的“打听”,让“我”极端惊讶、困惑以致无言以对,一颗不安的心一直悬到得知祥林嫂悄然死去。接下来的顺时叙就是交代是谁“杀”死了祥林嫂?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去深入展开意境层面的释读,那些回归顺时叙的故事情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逆时叙的开头,已经扩展了意境所覆盖的意义:祥林嫂死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鲁镇,才是由外而内逐步“杀”死祥林嫂的刽子手!顺时叙所交代的鲁四老爷、柳妈、卫老婆子、贺老六等相关人物的所作所为,无论虚伪、阴险、愚昧无知与否,不过都是封建文化的“附庸”乃至“牺牲品”,他们本身没有力量能毁灭祥林嫂,是封建文化给了他们种种有效的“毒剂”,才使得他们一个个成了毁灭祥林嫂的帮凶。也有人认为意境只有回归自然才成为意境,但换一种说法,意境回归人性也同样可以成为意境。固然,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小说的自然意境形态比较突出,然而,我们从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人物的人性层面去考察审美形态,也并非是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比如《祝福》结尾一段交代:“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段诗一般的结尾,语境有了。意境也有了,不管是反讽也好,还是以抒情为基调去诅咒一种文化也好,这段文字都体现了语境与意境的互相关联。“语境是说话人和受话人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系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⑤王一川在强调这一点时,也以《祝福》中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遭遇四婶“你放着吧!祥林嫂”一句话透心的刺激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为例,阐释了语境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性。所以说语境往往决定意境,意境实际上呈示的是一种话语含蓄效果。正是因为含蓄的魅惑,才诱发了想象并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到底是怎样的“天地众圣”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种意境覆盖下的含蓄就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猜想”抑或想象。至于含蓄的表现形式——话语蕴藉,王一川认为“是将现代‘话语’与我国古典文论术语‘蕴藉’相融合的结果。在文学艺术领域,特指汉语言文学作品中那种含蓄有余、蓄积深厚的状况。”⑥笔者同意这种说法,《祝福》的结尾就是一种含蓄性结尾,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读者。鲁镇的所谓“幸福”到底在哪里?或许只有天知道。说千道万其实就是一句话,作用于鲁镇种种意“象”中的语境与意境,是构成《祝福》叙事形态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以鲁迅为代表的汉语小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本土文化语境的制约,在小说叙事中也不知不觉地成为意境话语的践行者。小说立意明明是很确定的,但在叙述中总是“不作正面说明,而用委婉隐约的话把意见表达出来。”⑦不单《故乡》、《社戏》、《风波》、《白光》等小说这种委婉更为显而易见,即便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这些国民性批判色彩比较浓烈的小说,也不乏“以少寓多”、“小中蓄大”,即在有限之中蕴含无限的汉语小说叙事特质。阿Q虽然死了,但阿Q在读者的情感评价里,他与孔乙己、祥林嫂是殊途同归,只是阿Q的死比孔乙己的死影响面更大,比祥林嫂的死更有声有色,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呼叫。诚然,《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是凝重的,也是说不完的;其“无穷的启发”就有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其对于当时当世所延宕出来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意义至今也没有说完。不过,要真正发掘、释读《阿Q正传》其 “无穷的启发”,就要坚持“以中释中”抑或“以中释鲁”的思路,“无穷”显然是指在本土文化语境制约下的主题思想意义的“无穷”,也是意境审美层面的“无穷”,无疑,你无论怎么去想、也无论想得有多么多,也难以给“无穷”的言外之意以“穷尽”。与其说这是汉语小说叙事的技巧,还不如说这就是意境审美形态的魅力所在。中国小说家最为烂熟于心的一点是,汉语小说叙事有两个致命的关键词,一时故事性,二是话术,两者缺一不可。“所谓‘话术’,就是运用巧妙的言辞,以达成其高度形式的小说意识。”⑧西方学者可以把叙事看作是一种“修辞“,那么我们又何以不能把话语蕴藉也看作是一种”修辞“呢?从汉语言的角度说,所谓“修辞”强调的就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及其效果,即“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方法,恰当地表现与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活动。”⑨前面已经说了,鲁迅作为汉语写作的典范,他在小说叙事中塑造的每一个典型人物,既是鲁镇的“这一个”,也是修辞的“这一个”,其文化语境以及意境审美形态,都与小说叙事的意境审美观念息息相通,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无论从文化语境、还是从意境审美观念去考察鲁迅小说的叙事形态,是否践行“以中释中”的话语体系对于理解鲁迅及其小说的思想意义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坚持“以中释中”的话语思路与策略,是我们研究鲁迅释读鲁迅及其作品的一个最得体的方法,是“天经”,也是“地义”,同时也是对国有文化资源的积极继成与应用。因为鲁迅终究是汉语的“这一个”,其小说文本也终究是汉语的“这一种”,故而鲁迅及其小说作品的种种人物及思想和我们心中的某些文化积淀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只有积极从本土文化语境和意境审美观念去介入鲁迅的小说叙事文本,无论是研究还是批评,都会收到一种符合心理期待的预期效果:即鲁迅更能成为鲁迅,鲁迅小说也更能成为鲁迅小说。是的,坚持“以中释中”,我们与鲁迅的心也就会贴得更近一些。
注释:
①②杨义著:《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77页;第26页。
③程金城著:《原型批判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29页。
④方锡德文:《现代小说家的“意境”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03期,第64页。
⑤⑥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4版,第67页;第68页。
⑦⑨《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366页;第230页。
⑧谢昭新著:《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