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02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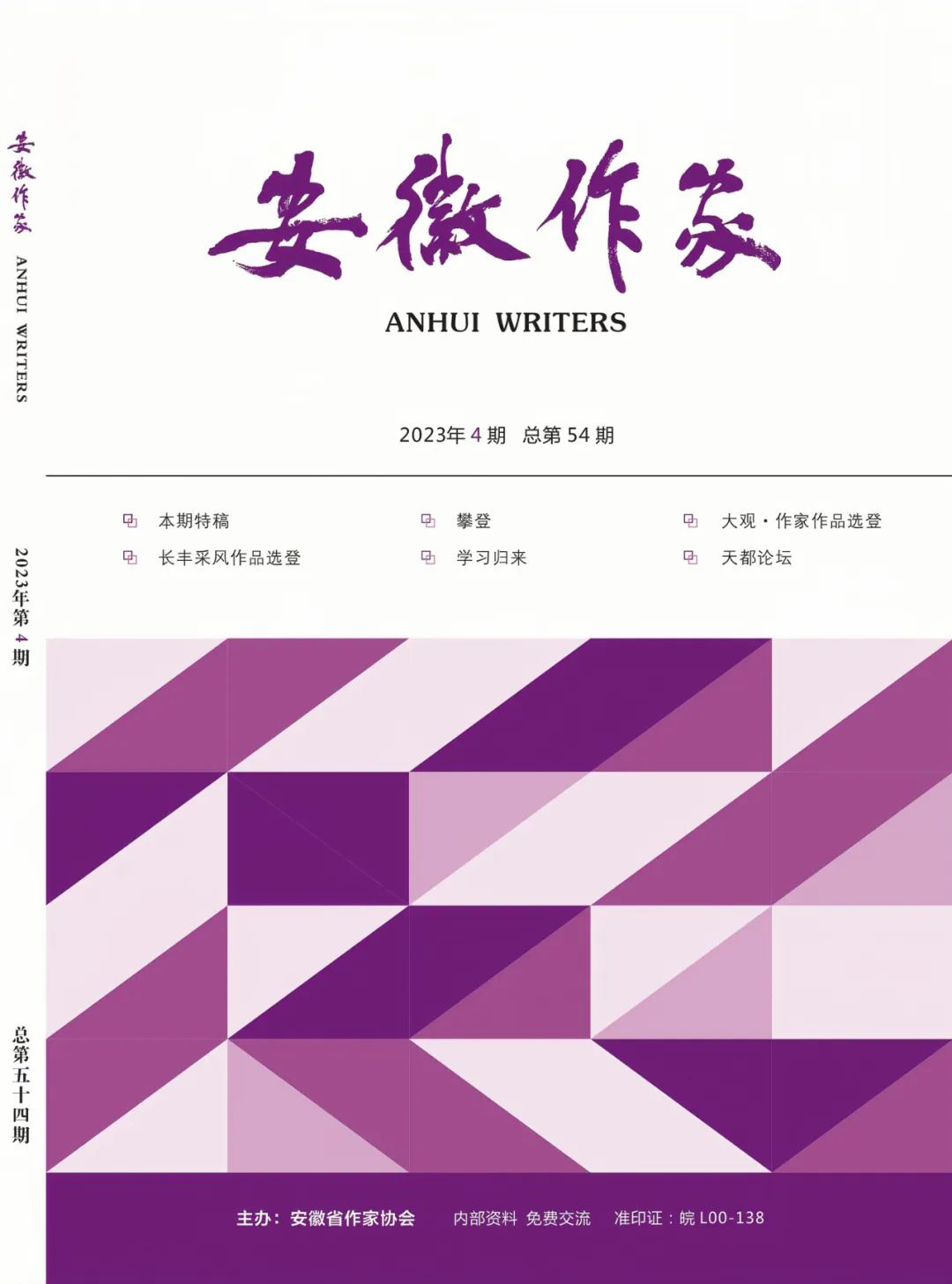
母亲的疼痛
梁厚云
自从那次意外摔倒,母亲像是变了一个人,似乎像是在清醒与糊涂之间挣扎,说不上是不是有些老年痴呆。她一直说肚子疼,轻则呻吟,重则撕心裂肺的喊叫。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拨打了120,心急如焚赶到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们没有查到疼痛的理由,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我们不太相信如此的正常,再三要求住院观察,可住院一周也没有查出病因,医生每天只给母亲挂一些葡萄糖和营养液之类的。住院十多天后,母亲说不疼了,自己要求出院。自那以后,肚痛的症状时而发生,住院成了家常便饭。
整个春节期间已经在哄着她过日子,她一直喊着要去住院。正月初八那天,漫天大雪,母亲“疼痛”加重,一天没有吃饭,我们只好再次把她送进医院。做完检查,一直医治母亲的医生笑着对母亲说,您的身体很健康,不需要住院,我们医院床位很紧张,您老人家做点好事,把床位留给别的病人。母亲听医生这么一说,安静了许多,用温和的目光看了看围在她身边的五个子女,喃喃说:没什大不了的,我们回家吧。
又是虚惊一场,从乡下赶来的大姐,不满地看了一眼母亲,放鞭炮似地说:家里四百头猪,行情又不好,我心不在肝上,你没病闹啥闹呀?说完,又怕惹母亲生气,俯下身,轻轻拥了一下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亲昵地说:我老大(妈妈的意思),你好好的,等我把猪卖了,给你买好吃的,买花衣服。母亲连连答应。二姐无奈地扫了众姊妹一眼,目光里满是幽怨和焦虑,她之前因在医院照顾母亲丢掉了工作,目前还在待业中。大哥交代了一些事,和母亲告别,他急需回合肥上班,母亲拉着大哥的手,眼巴巴地望着她唯一的儿子,声泪俱下,久久舍不得松开。我们五姊妹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说啥好。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手术后虽然恢复的还算不错,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大部分时间坐在轮椅上。在母亲没有摔倒之前,有哮喘病的老父亲一直由母亲照顾。面对二老都需要照顾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方案就是轮流过,五个子女,一轮还没有到头,事情来了。第一老父亲坚决不住城里的高楼高层,说是太闷,出不了气;第二母亲白天黑夜完全需要一个人照顾,除了大姐在家养猪自由一些之外,其余四个人均在上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父母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他们俩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医院度过,有好几次两个人一起住进医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小妹家小区附近租住了一楼的房子,由小妹专门照顾,其余四人付父母生活费和小妹的工资。
就这样,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的父母,住进了城里。租住的房子在月亮岛附近,风景好,热闹,更重要的是,小区一楼住的基本是老人,小区的环境虽然称不上一流,但也不差。租住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也干净整洁,加上小妹是整理家务活的能手,小家被她布置的特别温馨。门外廊檐放了一组半旧沙发,腿脚不便的母亲累了可以躺在沙发上面晒晒太阳。出租房外,每天都聚集很多老人在一起聊天,他们天南海北,东一句西一句,虽然聊的不算有条理,甚至不在一个话题上,但很开心。小妹心细,厨艺又好,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父母的笑容又回到了脸上,身体也恢复了。
可好景不长,住上不久,母亲的老毛病又犯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成天念叨着肚痛,要住院,要回乡下老家。不能如她的愿,就找茬怄气,和父亲吵架,数落子女对她不孝心。
我被母亲弄懵了,母亲之前完全不是这样。母亲一生遭受太多苦难,但她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一米五几的小个子母亲,走起路来像风,讲起话来像切葱一样干净利落,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可她说过很多有哲理的话,特别令我崇拜和折服。小时候家里断粮没有饭吃,瘦小的母亲从田里挑几个稻把回家,三下五除二打出稻谷,放在大锅里把稻谷熥干,然后再把熥干的稻谷放在地上用斧头一点点磕出米来,好几道工序,母亲一气哈成,舍不得休息一下。几个孩子都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等母亲把“加工”出来的大米放进锅里,再放一些白菜和一小团辣猪油,我们馋得口水都要出来了,那种菜米饭的香味至今还令我回味无穷。可饭好之后,母亲通常都会说肚子疼不想吃饭,等我们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过后,已所剩无几。母亲会把锅里剩下的锅巴烧焦,再放些水烧开,美其名曰:锅巴汤。母亲说,锅巴汤香,既管饿,又能暖肚子。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母亲的“肚疼”和锅巴汤的真正含义。
母亲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从小调皮惹事的我挨揍最多,有好几次把母亲气哭了。又加上家里女孩多,我顺理成章成了父母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懂事,念书成绩好于其她三姐妹,母亲对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中专落榜,我想上高中,因家里太穷,想上高中考大学是不可能的事,只能选择放弃,去了乡里一家涂料厂上班。在涂料厂,我干的全是体力活,又脏又累,全厂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当初去的时候,厂还处于建设阶段,白天干生产涂料的活,晚上还必须挑砖或抬砖。有一次,我在抬砖中摔倒,被倒下的砖头砸伤了腿和脚。母亲得到消息后,急匆匆赶到医院,看到我血肉模糊的腿和脚,放声大哭,使劲地用手捶着胸口。我劝母亲别哭,没事,一点都不疼,母亲不理睬我。只顾和厂方陪同我的人理论:要是有钱上学,她还这么小,还在上学呢!哪个愿意把小孩送给你们卖力啊!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她吗?呜呜呜,我疼,我心里疼啊!厂房陪同我的小领导,看到母亲那样,反感地扭头就走。母亲立刻止住哭泣,又说起道歉讨好之类的话来,那种卑微的眼神和肢体动作,深深刺痛了我。我知道母亲害怕我失去那份工作,只能委曲求全。我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不再让父母为我受委屈,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理想和现实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五姊妹中,除了哥哥考取中专,改变了命运,我们四姐妹均在底层挣扎。各自成家,生儿育女后,我们四人都活成了母亲的样子,单单为了活着就耗尽了所有,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自己的孩子,再苦再累再穷,我们都孝敬父母,不离不弃。当我做了母亲,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含义,理解了母亲的疼痛和坚强,继承了母亲善良、真诚、正直,牺牲自我的品行,过着简朴的日子。
人生如戏,上天赋予你的角色,你想不演可能吗?
大姐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大姐出嫁那天,细雨绵绵,大姐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我愤愤地注视着母亲,母亲竟然满脸泪水,哭得一塌糊涂。大了一点我才知道,父母包办大姐的婚姻,一半是因为男方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有粮食吃,母亲认为大姐嫁过去比在家里日子好过;一半是因为用了男方的一些彩礼钱,没有办法偿还人家。母亲用她自己方式爱大姐,替大姐做了决定,岂不知大姐心里有多痛。
二姐和大姐走向两个极端,有了大姐的前车之鉴,母亲对其余的三个女儿放宽了尺度。二姐自由恋爱,自作主张私奔了。对方穷得除了两间茅草屋,一无所有。母亲几经周折找到二姐后,目睹二姐穷困潦倒的家,嚎啕大哭。可以想象,母亲当时是多么的痛心和崩溃。
我成熟得晚,在结婚之前天真幼稚的近乎于可笑,连我对象个子不高,我也认为那不要紧,他还会长高的。我懵懵懂懂,傻啦吧唧的,把一切想得简单美好。谁知婚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更加恶劣的环境击碎了我的梦想。好在我是个倔强的人,哭过、痛过、崩溃过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就如当年体重九十斤的我硬生生把一袋袋一百一十来斤的稻谷扛在肩上一样。虽然我从不向母亲诉说我的难处,从来只报喜不报忧,可母亲不傻,她都看在眼里,是瞒不住的。
小妹是被父母宠坏掉的女孩子,在婚姻的事上挑三拣四,目睹三个姐姐的命运,她害怕了,立志非城里人不嫁。三十多岁嫁给了一个没车没房,并且没有正式工作的城里人,生活的不易可想而知。母亲因为小妹,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大哥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他的生活,是我们姐妹四人一直企望不到的高度,有份体面的工作,很多年前就有车有房。可母亲还是对他放心不下,处处洞察大哥的生活细节,生怕他过得不幸福,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母亲便寝食难安。母慈子孝,至今母子俩一天最少要通一次电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一生操心太多,痛点也太多,每一个孩子都牵扯她的心,现在老了,她貌似不太关心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自己身上。是老年痴呆导致的臆想症,恐惧死亡?还是人老了没事做,想磨人,不得而知。
母亲是幸福的,四代同堂,其乐融融,第三代人中大学生、研究生比比皆是,教师、医生、公务员、工程师等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还有我父亲的陪伴。快九十岁的人了,白头偕老,不离不弃,还夫复何求?
我想把如此这般的幸福传递给母亲,希望能治愈她的疼痛。我坐在母亲床前,母亲习惯性地握着我的手,我循循善诱,话还没有讲到一半,母亲睡着了。睡梦中的母亲呢喃着:我疼……我要回家……疼……
有家的地方没有子女照顾,有子女照顾的地方算不上家。母亲辛劳一生,落下一身疼痛,人生的暮年居无定所,有家不能归,只能漂泊……
眼泪顺着母亲的眼角流下,布满皱纹的脸抽搐着,母亲瘦了,一天不如一天。我轻轻擦去母亲眼角的泪水,不料自己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母亲的手上,母亲的手抽动了一下,我把母亲的双手攥得更紧了。
窗外,月亮朦朦胧胧镶嵌在两栋高楼之间,月光如水一般清澈。明天一定是个晴朗的日子。

梁厚云,安徽六安人,创作有多部电影剧本、小说。